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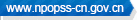
社科要聞學(xué)壇新論工作動(dòng)態(tài)通知公告最新成果集萃資助學(xué)術(shù)期刊學(xué)者傳真學(xué)者專欄機(jī)構(gòu)設(shè)置聯(lián)系我們
項(xiàng)目申報(bào)與管理項(xiàng)目動(dòng)態(tài)成果管理成果發(fā)布經(jīng)費(fèi)管理各地社科規(guī)劃管理項(xiàng)目數(shù)據(jù)庫專家數(shù)據(jù)庫歷史資料
【內(nèi)容提要】 謝崛的文章包含一系列謬誤,一是對(duì)中西形而上學(xué)本身的構(gòu)成方式有誤解,因?yàn)橹袊鴤鹘y(tǒng)形而上學(xué)不僅僅是實(shí)踐論的,而西方形而上學(xué)也不僅僅是認(rèn)識(shí)論的,雙方的比較應(yīng)該建立在這些要素的結(jié)構(gòu)模式上,而不是有無某種要素上,否則是失之簡單化的;二是對(duì)哲學(xué)史的諸多事實(shí)作了錯(cuò)誤的描述,如對(duì)亞里士多德存在論的誤解和斷言康德以前沒有人把形而上學(xué)與實(shí)踐的人相聯(lián)系,以及對(duì)西方偽善觀的膚淺化,對(duì)康德自由觀、黑格爾“現(xiàn)實(shí)的就是合理的”命題的誤讀等等,都表明他對(duì)西方哲學(xué)史不太熟悉;三是對(duì)這些事實(shí)的評(píng)價(jià)帶有一種錯(cuò)位的偏見,這種偏見站在西方社會(huì)的角度看也許是有道理的,但放在中國社會(huì)的語境中卻展示了一種“圍城”現(xiàn)象;四是在善惡觀、自由觀、反思觀、信仰觀等等方面都體現(xiàn)了一種強(qiáng)烈的種族主義傾向,這是不利于對(duì)理論問題的澄清的。
【關(guān) 鍵 詞】中西哲學(xué)比較/形而上學(xué)/邏輯理性/直覺悟性/圍城
有幸讀到謝崛博士與我對(duì)話的文章《形而上學(xué)的迷惑》①(以下簡稱為“謝文”),啟發(fā)良多。謝博士花了不少功夫來讀我的幾本書,并由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這使我在感謝之余,也有了一種回應(yīng)的義務(wù)。下面我就謝博士所提出的七個(gè)方面的質(zhì)疑逐一回應(yīng),以就正于謝博士。
一、形而上學(xué)觀
謝文一開始就批評(píng)我的思想中有很多偏頗和自相矛盾之處,“這表現(xiàn)在他的善惡觀、自由觀、認(rèn)識(shí)觀、反思觀、信仰觀、實(shí)用觀、語言觀等諸多問題上。這些問題看起來很多,但實(shí)際上都是哲學(xué)中最基本的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gè)人的哲學(xué)觀或形而上學(xué)觀而展開的”。這樣看來,謝文所提出的七個(gè)方面的問題(“信仰觀和實(shí)用觀”合并為一個(gè))中,“形而上學(xué)觀”是最核心的,所以首先要提出來討論。那么,謝文如何提出問題呢?他說:
中國學(xué)術(shù)界在“是西方的形而上學(xué)強(qiáng)勢,還是中國的形而上學(xué)強(qiáng)勢”問題上頗多爭議……回答這個(gè)問題,首先必須分清這樣兩個(gè)方面,即形而上學(xué)究竟只是認(rèn)識(shí)論的問題還是既是認(rèn)識(shí)論的問題,更是實(shí)踐論的問題。如果是前者,那西方的形而上學(xué)無疑強(qiáng)勢;而如果是后者,那中國的形而上學(xué)肯定強(qiáng)勢。我覺得,這樣提出問題未免太簡單化了,有點(diǎn)像幼兒園小朋友吵嘴:“你爸爸厲害還是我爸爸厲害?”我不太清楚謝文所謂的“強(qiáng)勢”究竟是指什么,是更好、更有效?規(guī)模更龐大、更深刻?還是可以把對(duì)方包括進(jìn)來?好像都不是。他說:“西方哲學(xué)在認(rèn)識(shí)論上一向是占有優(yōu)勢的。”從這句話判斷,應(yīng)該是指西方人對(duì)認(rèn)識(shí)論研究得比較多些。而“中國的哲人們很少乃至幾乎無人從認(rèn)識(shí)論的角度來探討形而上學(xué)問題。相反,他們把注意力放在了人的行為實(shí)踐和社會(huì)關(guān)系上,而形而上學(xué)只是他們的本體依據(jù)”。從這里我們所得出的結(jié)論只能是,西方形而上學(xué)在認(rèn)識(shí)論上有強(qiáng)勢或“優(yōu)勢”,而中國形而上學(xué)在實(shí)踐論上有強(qiáng)勢或“優(yōu)勢”;但是,我們無法從總體上比較兩種形而上學(xué)的強(qiáng)勢或優(yōu)勢,更不能得出謝文想要的結(jié)論,即“中國的形而上學(xué)肯定強(qiáng)勢”,除非他設(shè)定“實(shí)踐論比認(rèn)識(shí)論優(yōu)越”這一前提。但這一前提本身恰好是需要證明的。然而,他證明的不是實(shí)踐論比認(rèn)識(shí)論更優(yōu)越,而是引用康德的觀點(diǎn)說,“形而上學(xué)不是一個(gè)認(rèn)識(shí)問題,而是一個(gè)信仰和實(shí)踐的問題”。照這種理解,那么問題就不是中西形而上學(xué)哪個(gè)更“強(qiáng)勢”,而是哪個(gè)更是形而上學(xué)。換言之,西方認(rèn)識(shí)論的形而上學(xué)不是形而上學(xué),只有中國實(shí)踐論的形而上學(xué)才是形而上學(xué)。這種結(jié)論,恐怕連謝博士自己也無法認(rèn)可。
更何況,謝文對(duì)西方哲學(xué)的這種理解也是不準(zhǔn)確的。比如,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xué)就不是單純的認(rèn)識(shí)論,而且同時(shí)就是本體論(或存在論,ontology);而“作為存在的存在”也不像謝文所講的,“這種存在只能是‘神’”,甚至是“思想本身”,而是作為“第一實(shí)體”的“個(gè)別實(shí)體”,如“蘇格拉底”或“這匹馬”。② 由這種個(gè)別實(shí)體的存在到神(或“對(duì)思想的思想”)還有漫長的路程,而貫通這一路程的內(nèi)在法則就是包含善和實(shí)踐要素在內(nèi)的目的論。其實(shí),早在柏拉圖那里,作為最高本體、最高存在的“善的理念”就是著眼于倫理學(xué)和實(shí)踐哲學(xué)的了,而后來的康德實(shí)踐哲學(xué)正是從他這里引申出來的。康德指出:“柏拉圖最初是在一切實(shí)踐的東西中,就是說,在一切以自由為依據(jù)的東西中,發(fā)現(xiàn)他的理念的,而自由本身則是從屬于那些作為理性之一種特有產(chǎn)物的知識(shí)之下的。”③ 所以,不論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后來的哲學(xué)家,決不是如謝文所斷言的“完全忽視了它[形而上學(xué)]與作為實(shí)踐個(gè)體的人的聯(lián)系和人在形而上學(xué)體系中應(yīng)有的地位”。謝博士以為,“在西方形而上學(xué)發(fā)展史中截止到黑格爾,唯有康德把形而上學(xué)和作為實(shí)踐的人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由此看出,他對(duì)西方哲學(xué)史的確不太熟悉。④
當(dāng)然,與中國哲學(xué)相比,西方哲學(xué)在康德以前雖然不是完全忽視人的實(shí)踐,但至少是把認(rèn)識(shí)凌駕于實(shí)踐之上的。這一傳統(tǒng)從蘇格拉底將美德歸結(jié)到知識(shí)上來就已經(jīng)開始了,并且經(jīng)久不衰,直到康德提出“實(shí)踐理性高于理論理性”為止。相反,中國哲學(xué)則是從道德實(shí)踐的角度來探討認(rèn)識(shí)論的,但也決不是像謝文所說,“幾乎無人從認(rèn)識(shí)論的角度來探討形而上學(xué)問題”。例如,張載講,“有識(shí)有知,物交之客感爾”,“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nèi)外之合也”。⑤ 這顯然是從主客二分的角度來談?wù)J識(shí)的。只不過張載對(duì)于這種“聞見之知”不是十分看重,他重視的是道德良知:“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⑥ 他深受老子的影響,將道家的直覺體悟與儒家的內(nèi)心良知結(jié)合成了一種對(duì)天理天道的高級(jí)認(rèn)識(shí)論。自孟子以來的良知說固然不是一種外部自然知識(shí),但作為道德知識(shí)本身當(dāng)然也是一種認(rèn)識(shí)論,只是這種認(rèn)識(shí)發(fā)源于人心中的道德體驗(yàn),是在待人接物的日常道德實(shí)踐中激發(fā)出來的。由此觀之,中西形而上學(xué)的比較恐怕不能夠像謝博士所做的那樣,從西方抽出“認(rèn)識(shí)論”,又從中國抽出“人的實(shí)踐”,來做一種簡單化的對(duì)比;更不能像他那樣,認(rèn)為講認(rèn)識(shí)論就一定會(huì)“陷入脫離人的實(shí)踐那種無休無止的認(rèn)識(shí)論的怪圈”,而訴之于“悟覺體悟”則必定會(huì)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其與現(xiàn)代理論物理學(xué)的深層吻合”而取得西方形而上學(xué)“望塵莫及”的“強(qiáng)勢”。至少,這種斷言的跳躍性過大,隨意性和情緒性過強(qiáng)。我們應(yīng)該做的毋寧是對(duì)中西形而上學(xué)進(jìn)行一種結(jié)構(gòu)模式的比較,即考察兩種形而上學(xué)中各自的認(rèn)識(shí)論和本體論、自然知識(shí)和道德(實(shí)踐)知識(shí)之間的不同關(guān)系模式,并分析其成因。一般說來,中西形而上學(xué)在構(gòu)成的成分上并沒有根本的區(qū)別,都是既有認(rèn)識(shí)論也有本體論,既有理論方面也有實(shí)踐方面,區(qū)別只在于這些成分的構(gòu)成模式(誰依賴于誰)。
所以,在我看來,如果單純從理論上來評(píng)價(jià)的話,中西形而上學(xué)之間并不存在一個(gè)所謂優(yōu)劣問題,中國人向西方學(xué)習(xí)與西方人向中國學(xué)習(xí)都是必要的、正當(dāng)?shù)模际窃趶浹a(bǔ)自己的不足。但作為一個(gè)中國人,我們更應(yīng)該看到,西方人的“形而上學(xué)的迷惑”雖然使人困擾,但同時(shí)也正表明他們尚未喪失掉對(duì)未知事物的探索精神;中國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xué)的自信”雖然給人一個(gè)良好的自我感覺,但也可能隱藏著某種自欺。例如,謝文說,西方人之所以愛智慧,是因?yàn)樗麄儭叭狈χ腔邸保袊酥圆粣壑腔郏笆且驗(yàn)橹袊颂挥谥腔哿耍∷詻]有必要再去‘追求’智慧,而只需把他們的智慧用于生活與實(shí)踐就可以了”。這不是典型的虛驕自大嗎?中國智慧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jīng)“完成”了,這難道不是今天中國人的悲哀?我不知道謝博士是否已加入了澳洲籍,如果是以一個(gè)外國人的身份來夸獎(jiǎng)中國(古代)智慧,那倒無可非議,反而顯得大度;但看來他還是自居為中國人的,并且還想以此振作起中國人的“自信”,這問題就大了。這種“自信”無非是故步自封或自大的飾詞。
另一方面,如果聯(lián)系中國現(xiàn)代一百多年的實(shí)踐來評(píng)價(jià),那么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西方形而上學(xué)對(duì)中國形而上學(xué)的確呈現(xiàn)出不可抗拒的“強(qiáng)勢”。在今天,不少人已經(jīng)指出,不懂西方哲學(xué)的人,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國哲學(xué)。現(xiàn)代中國人凡在中國哲學(xué)上做出一定開拓或貢獻(xiàn)者,無一不是匯通中西的大家。就連謝博士本人,不也要用西方的普利高津等人的名頭來加強(qiáng)自己的自豪感嗎?反之,不懂中國哲學(xué)的人,在對(duì)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的推進(jìn)方面卻并無大礙,西方哲學(xué)大師借中國哲學(xué)說事的人很少。當(dāng)然,也許將來他們會(huì)意識(shí)到中國哲學(xué)的長處,但我們不能現(xiàn)在就預(yù)支將來的可能性,我們要解決的是自己當(dāng)前的嚴(yán)重問題,即中國形而上學(xué)如何通過學(xué)習(xí)西方而“做強(qiáng)”的問題。
總的來看,中西形而上學(xué)的關(guān)系在當(dāng)代處于兩種不同的處境,一是對(duì)于中國人來說,我們必須努力學(xué)習(xí)和吃透西方形而上學(xué)的精髓,而不能滿足于淺嘗輒止;另一方面,對(duì)于西方人來說,他們應(yīng)該、且也已經(jīng)有一小部分人開始注意到中國哲學(xué)的獨(dú)到之處。這種處境頗類似于錢鍾書的“圍城”:城里面的人拼命想出來,城外的人則努力想進(jìn)去。撇開語境,籠而統(tǒng)之地說什么“強(qiáng)勢”或“劣勢”是沒有意義的。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說話的人是處于“城里”還是“城外”。而這種處境意識(shí),恰好是謝博士所缺乏的。
 |
(責(zé)編:張湘憶(實(shí)習(xí))、張湘憶)
 紀(jì)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xué)出土文獻(xiàn)研究與保護(hù)中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舉行【詳細(xì)】
紀(jì)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xué)出土文獻(xiàn)研究與保護(hù)中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舉行【詳細(xì)】
→ 國家社科基金同行評(píng)議專家數(shù)據(jù)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