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費冬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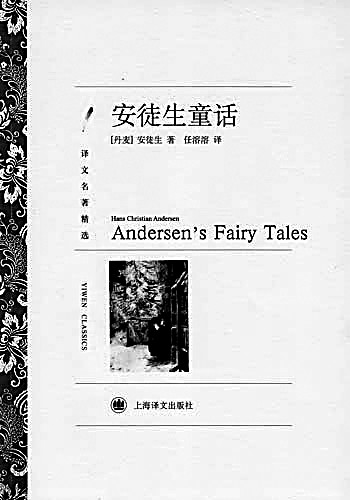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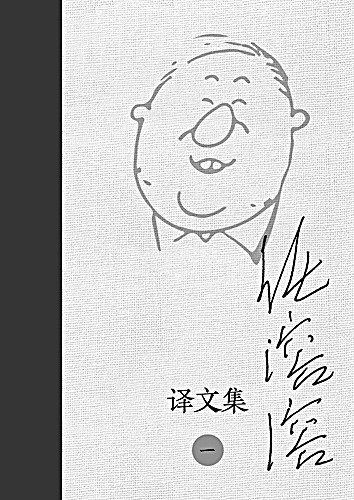

1979年2月,在《少年文藝》編輯迎春座談會上,賀宜、陳伯吹、茹志鵑、徐遲、任溶溶、杜宣(從左至右)在一起。
學人小傳
任溶溶(1923—2022),本名任以奇,筆名任溶溶,廣東鶴山人,生于上海。翻譯家、兒童文學作家。1945年畢業(yè)于上海大夏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副會長、上海語文工作者協(xié)會副會長、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曾獲中國翻譯協(xié)會“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著有《丁丁探案》《沒頭腦和不高興》《一個可大可小的人》等。譯有《安徒生童話》《木偶奇遇記》《洋蔥頭歷險記》《彼得·潘》《長襪子皮皮》《吹小號的天鵝》《夏洛的網(wǎng)》等。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翻譯第一篇外國文學作品,到2022年去世,任溶溶的翻譯生涯持續(xù)了七十多年。在這漫長的時間跨度里,他在兒童文學翻譯領(lǐng)域眼光之準、魄力之大、用力之專,翻譯作品數(shù)量之多、質(zhì)量之高、涉及的語種和作家之廣、引發(fā)的反響之大,都是整個翻譯界獨一無二的存在。他的貢獻和付出,得到了翻譯界、文學界和讀者的普遍認可和高度評價,他先后獲得了“陳伯吹兒童文學獎·杰出貢獻獎”“宋慶齡兒童文學獎·特殊貢獻獎”“國際兒童讀物聯(lián)盟翻譯獎”等多個重要兒童文學獎項。著名文學評論家束沛德稱,“他的文質(zhì)兼美的等身著譯,是我國兒童文學高地上一座令人矚目的豐碑”。另一位文學評論家劉緒源則認為:“在中國文壇上,翻譯兒童文學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變了中國的兒童文學。”
遇見兒童文學是任溶溶的幸運,而遇見任溶溶也是中國兒童文學和中國兒童的幸運。
/走上翻譯兒童文學之路/
任溶溶,祖籍廣東鶴山,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上海。原名任根鎏,后改名任以奇。任家早年生活貧苦,任父年輕時遠赴日本,在一個同鄉(xiāng)開的印刷所當學徒,后回到上海繼續(xù)從事印刷生意。經(jīng)過多年打拼,到任溶溶出生之際,任家的經(jīng)濟條件已經(jīng)大為好轉(zhuǎn),擁有了木器店、紙行和印刷所等產(chǎn)業(yè)。
任溶溶5歲時被父母帶到廣州,留給親人照顧,父母仍舊回上海做生意。在廣州,他先是進私塾讀書,后到嶺南大學分校小學部讀小學。任溶溶從小愛讀書,起初,他的讀物以傳統(tǒng)小說居多,如《三俠五義》《小五義》《續(xù)小五義》《三國演義》《濟公傳》等。他最喜歡好玩有趣的《濟公傳》。后來他嫌家里的書不夠讀,就把目光投向家附近的文化街,“一家家書店跑,一家家書店看書”。嶺南大學分校小學部的圖書館配書很豐富,正是在這個圖書館里,任溶溶開始接觸中外兒童文學,并為之深深著迷,經(jīng)常在別的小朋友們午睡之際,跑到圖書館讀書。葉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稻草人》、開明書店翻譯的《木偶奇遇記》等,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些童書中,他最愛讀《木偶奇遇記》,這本書后來在他的翻譯生涯中也占據(jù)著重要位置。
1938年,任溶溶隨親戚回到上海。此時,上海已被日軍占領(lǐng),任家的店鋪僥幸搬進了租界。重視子女教育的父親將任溶溶送進雷士德中學讀書。這是一所英國人辦的學校,對于英語學習很重視,除了國文、中國地理用中文授課之外,其余課程都用英文教學。耳濡目染加之個人的勤奮努力,任溶溶的英語水平有了較大提升,在精通俄語的同學盛峻峰(翻譯家草嬰)的鼓勵下,他還開始自學俄語。在校期間,任溶溶受進步思想影響,初三那年和同學一道去蘇北參加新四軍,在部隊待了半年。中學畢業(yè)后,在地下黨的領(lǐng)導下,他從事了一段短暫的新文字改革工作。1942年,經(jīng)組織安排,任溶溶進入大夏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在大學,他一方面涉獵更多的外國文學著作,把當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里的外國文學作品基本讀了一遍,另一方面,又跟隨郭紹虞、周予同等著名學者讀書,對文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45年,任溶溶從大夏大學畢業(yè)。在偶然的機緣下,他翻譯了第一篇兒童文學作品《黏土做的炸肉片》,刊發(fā)于1946年1月出版的《新文學》雜志創(chuàng)刊號。那段時間,任溶溶的一位大學同學在兒童書局編《兒童故事》雜志,因刊物缺稿,便邀請英語不錯的任溶溶幫忙譯稿,任溶溶一期譯一篇,翻譯了十幾篇迪士尼圖畫故事。1947年,任溶溶的女兒出生,童心未泯的他用女兒的名字“任溶溶”當了筆名。同年,時代出版社社長姜椿芳與任溶溶結(jié)識,邀請他翻譯蘇聯(lián)兒童文學作品。就這樣,任溶溶開始了他的兒童文學翻譯生涯。
/堅守真善美/
新中國成立后,任溶溶先后在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今上海人民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等機構(gòu)擔任編輯,雖然工作單位發(fā)生了幾次變化,但他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熱情一如既往。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nèi)兒童文學讀物比較匱乏,雖然有一些老作家如張?zhí)煲怼㈥惒怠①R宜、嚴文井等繼續(xù)從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但總體上,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比較單薄。這時,作為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編輯,任溶溶組織人手翻譯了不少兒童文學書籍。同時,他本人也身體力行,翻譯了大量作品。
那段時間,任溶溶所譯大多為蘇聯(lián)兒童文學作品。在兒童詩領(lǐng)域,他翻譯了馬雅可夫斯基、馬爾夏克、巴爾托、米哈爾科夫、楚科夫斯基等詩人的作品。他喜歡馬爾夏克詩歌的韻律和節(jié)奏,也看重其詩的宣傳鼓動價值,《給小朋友的詩》《給新少年講講舊日子》《對留級生說的話》等譯作引起了較多的關(guān)注和較大的反響。十幾年后,有人聲稱要“打倒中國的馬爾夏克——任溶溶”,謙遜的任溶溶一度為此感到心虛,覺得自己配不上“中國的馬爾夏克”這個稱號。此外,他還翻譯了《我們的工廠》《一年級小學生》《森林變成了城市》《大晴天》《小草兒歷險記》等兒童小說,《雪女王》《神氣活現(xiàn)的小兔子》《白天使》《十二個月》等兒童劇作品,《洗呀洗干凈》《在藍色大海的邊上》《哈哈鏡王國歷險記》等童話,以及《我的會演戲的鳥獸》《古麗雅的道路》《列寧的故事》《進攻冬宮》等兒童讀物。
任溶溶看重兒童文學的教育價值,認為一個好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同時兼具思想教育價值、藝術(shù)教育價值和語文教育價值。他選擇的多數(shù)兒童文學作品,都能體現(xiàn)這三種價值。20世紀50年代初,全國開展愛國衛(wèi)生運動,但是國內(nèi)缺乏衛(wèi)生教育主題的兒童讀物,任溶溶就翻譯了《洗呀洗干凈》這本童話。該書主要講述了一個不愛清潔的小朋友經(jīng)歷一系列事件后發(fā)生轉(zhuǎn)變的故事。這本合乎時宜的童書出版后,受到中小學生的歡迎。
任溶溶既注重譯作的教育價值,也具備良好的審美判斷力和扎實的翻譯實力,因此他的很多作品都一版再版,影響了幾代小讀者。典型的如《古麗雅的道路》,這本書1953年3月由時代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蘇聯(lián)作家葉列娜·伊林娜,原名《第四高度》,寫的是活潑可愛的小女孩古麗雅在老師、家長、社會的引導下,改正缺點,克服困難,成長為女英雄的故事。這本書出版不到一年的工夫,就已經(jīng)三次印刷,印數(shù)近50萬冊,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一起成為譯文界的“紅色經(jīng)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等媒體上都刊發(fā)了書評。葉圣陶專門寫了《讀〈古麗雅的道路〉》,高度評價此書。作家李佩甫幾十年后深情回憶:“正是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也由此改變了我的生活軌跡。這是一本有氣味的書:面包的味道、果醬的味道,還有沙發(fā)、桌布和羊毛地毯的味道。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面包,但在中國最饑餓的年代,我卻吃到最鮮美的‘面包’。”(李佩甫《平原是我的寫作領(lǐng)地》)
任溶溶在翻譯上精益求精,有時候到了較真的地步。《小草兒歷險記》這本書,他原本已經(jīng)根據(jù)1949年的俄文版完成了翻譯,看到此書于1951年出了新的版本,于是,又依據(jù)新版本重新校改了一遍。類似的,還有《大晴天》一書,1951年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譯本是從1948年俄文版譯出的,1954年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任溶溶新譯本則是根據(jù)1953年的俄文新版進行翻譯的。
從1949年到1963年,任溶溶的翻譯作品有40多部,這還不算單篇作品。他因此成為這個時期著作最為豐碩的幾位兒童文學翻譯家之一。
/遍尋風雅頌/
“文革”期間,在艱難的處境下,任溶溶雖然沒有翻譯作品,但充分利用時間,自學了意大利語和日語。到新時期來臨之際,他已經(jīng)熟練掌握了四門外語:俄語、英語、意大利語和日語,這為他后來的翻譯事業(yè)奠定了語言基礎(chǔ)。
1978年10月,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工作座談會在江西廬山召開。會議由國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等七家單位聯(lián)合舉辦,號召恢復少兒讀物的出版工作,盡快解放思想,多出好書;明確提出要考慮兒童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理解水平,把作品寫得生動有趣。用束沛德的話說,“這次廬山會議結(jié)束了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出版界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局面,揭開了我國新時期兒童文學的新篇章”(束沛德《兒童文學的廬山緣》)。參與了這次會議的任溶溶,深受鼓舞,心中又燃起了翻譯的熱情。“下山之后,業(yè)余除了創(chuàng)作,一口氣還翻譯了好多部兒童文學作品,一年當中譯了二三十萬字。”(《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梳理任溶溶這個階段的翻譯成果可以發(fā)現(xiàn),自1979年起,他每年都有譯作出版,有時一年就出版10部以上。
任溶溶進行兒童文學翻譯的關(guān)鍵是精選作品。他曾自白,他翻譯兒童文學有兩個目的,一是為中國兒童挑選優(yōu)秀作品,二是給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提供借鑒。他堅守藝術(shù)標準和思想標準,選擇那些優(yōu)質(zhì)兒童文學作品進行翻譯。任溶溶不僅深愛文學,對美術(shù)、音樂、戲劇、電影也有較廣泛的涉獵,而精通四門外語,則讓他具備了非凡的視野。故而他總是能從海量兒童文學作品中挑選出藝術(shù)價值高、成就大的作品來翻譯。任溶溶這時已經(jīng)意識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兒童文學翻譯事業(yè)的結(jié)構(gòu)性缺陷,即優(yōu)秀的蘇聯(lián)兒童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有了譯本,但其他國家的優(yōu)秀兒童文學作家作品還沒有得到充分介紹。為此,他翻譯了大量歐美經(jīng)典作品,尤其是歷屆國際安徒生獎得主的作品。在翻譯策略上,他一方面精選單部優(yōu)質(zhì)作品,翻譯了《木偶奇遇記》《小茶匙老太太》《借東西的地下小人》等公認的精品;另一方面,還采取專題的方式,力圖將幾位國外兒童文學大家的代表作甚至全部作品都譯介過來,讓中國兒童和兒童文學作家對這些國外優(yōu)秀作家作品有系統(tǒng)的了解。其中,羅大里、林格倫、羅爾德·達爾、托芙·楊松、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休·洛夫廷是任溶溶重點翻譯介紹的幾位兒童文學作家。
以瑞典作家林格倫為例,從1980年到1983年,短短幾年,任溶溶翻譯了《住在屋頂上的小飛人》《小飛人又飛了》《長襪子皮皮》《瘋丫頭瑪?shù)锨俚墓适隆返?3部作品。這些作品里塑造的皮皮、卡爾松等多個頑童形象,正是當時中國兒童文學界有所缺失的,它們不僅打開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和讀者的新視界,也大大促進了中國兒童文學新發(fā)展格局的形成。此后,他還翻譯了意大利作家羅大里的《洋蔥頭歷險記》《電視迷歷險記》《藍箭號列車歷險記》《假話國歷險記》四部作品,及美國作家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的《精靈鼠小弟》《吹小號的天鵝》《夏洛的網(wǎng)》三部力作。他尤其偏愛美國作家休·洛夫廷的童話,在2002年79歲高齡之際,還將《杜立特醫(yī)生故事全集》一股腦地全部翻譯成中文。
任溶溶對重點作家長篇小說和童話的譯介,一直持續(xù)到2004年。此后,年事漸高的任溶溶,精力不如從前,譯介重心有所轉(zhuǎn)移,由大部頭的長篇兒童小說、童話、詩歌、話劇的翻譯,轉(zhuǎn)向短小精致的繪本譯介。繪本雖然語言比較簡單,但因為讀者對象是年幼的孩子,作品的音韻、節(jié)奏等需要適合他們的年齡特點,“老小孩”任溶溶翻譯起繪本得心應手。其實,如前所述,早在新中國成立前,任溶溶就曾譯介過十幾本迪士尼圖畫書。20世紀50年代,他又翻譯了四五十本圖畫書。
任溶溶翻譯繪本的熱情是如此高漲,有時一年就出版40多本。這些譯介繪本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單本繪本,如《咕嚕牛》《一片葉子落下來》《誰要一只便宜的犀牛》《會說話的骨頭》;二是系列繪本,如“花格子大象艾瑪系列繪本”“五只小猴子系列繪本”“溫妮女巫魔法繪本”。在新作不斷問世的同時,任溶溶早年的童書譯作也被一版再版,“任溶溶”這個名字在21世紀中國孩童的書架上大放異彩。
/新釋信達雅/
任溶溶的翻譯作品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或者說,有著“任溶溶印跡”。這和他秉持“兒童本位”的翻譯觀是分不開的。任溶溶特別強調(diào)讀者意識,認識到“兒童文學翻譯有一個特點,就是讀者對象十分明確,是孩子,而且不是籠籠統(tǒng)統(tǒng)的孩子”(任溶溶《我譯兒童文學》)。他認為,幼兒、小學低年級和高年級的孩子閱讀需求有所不同,要根據(jù)他們的年齡特征選擇翻譯策略。給幼兒譯外國詩歌,自然要譯成兒歌的樣子,朗朗上口,但給大孩子譯書就不能有娃娃腔,因為半大孩子,都不希望別人把他們看作小娃娃。
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曾表達過翻譯的不易,稱“譯事三難:信、達、雅”。在“信、達、雅”三原則中,任溶溶對“信”最為看重,總是努力將原作的美原汁原味地傳達給中國兒童。他說:“譯者就好比一位演員,要揣摩不同人物,表現(xiàn)不同風格。演員投入一個角色,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把原作盡可能貼切地翻譯過來。原作者風格各異,翻譯的時候也應保留原來的風格,我覺得翻譯就是一個字——‘信’,不但文字,整個作品都要忠實于原著。”(《任溶溶:與安徒生相伴到老》)不僅文字,連人物說話的口氣他都努力做到和原作相像,他堅持認為“譯者既要對得起讀者,也要對得起作者,要務使外國作家有味的文字不變成無味的文字”(《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
任溶溶既尊重作者的原創(chuàng)風格和特色,又充分考慮中國兒童讀者的閱讀喜好和接受心理,努力做到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達”。他說:“兒童書的讀者對象再明確不過,是小朋友。作者們的書,就是為小朋友寫的。因此譯出來的兒童書,要讓小讀者讀起來順當,覺得有趣。他們又正值學語文的時候,譯文要規(guī)范,我盡可能爭取這樣做,盡可能做到像一位外國作家借用我這個中國譯者的口,把他的書用中國話講給中國小讀者聽。”(任溶溶《譯者職業(yè)像演員》)兒童喜歡讀有節(jié)奏感、句式相對簡單,而表達又很生動的作品,為了讓他心中的小讀者滿意,任溶溶的翻譯并不一味追求文字的典雅,反而盡量讓表述口語化,多用短句、疊詞、擬聲詞、重復的詞組,努力讓譯文通俗易懂。如《安徒生童話》的翻譯,面對同一個句子“I quacked and clucked, but all to no purpose”,翻譯家葉君健是這樣翻譯的:“我說好說歹,一點用也沒有!”而任溶溶的翻譯是:“我又是好好地說又是嘎嘎嘎地叫,但是一點用處也沒有。”葉譯注重簡練,選用了成語,而任譯為了更容易被兒童理解,選用了擬聲詞。有時候原文有文字游戲——這在兒童文學作品中經(jīng)常可見,考慮到中外文音韻節(jié)奏之間的差異,任溶溶并不死板直譯,而是用相應的中文文字游戲來替代,讓中國孩子讀起來順當、開心。雖然字面上沒有完全忠實于原文,但這與原作的游戲精神是一致的。
至于“雅”,在任溶溶的譯作里則呈現(xiàn)出了另一種特色。任溶溶并不把華麗的辭藻視作翻譯之雅,而是堅守兒童文學翻譯的“素樸之美”,從素樸中覓童趣,從素樸中見深情。任溶溶的譯文雖然口語化,卻很講究音韻,淡而有味,孩子讀了覺得好懂,家長讀了則可體味到言外之意和韻外之旨。以《夏洛的網(wǎng)》中的部分譯文為例:“So while the children swam and played and splashed water at each other. Wilbur amused himself in the mud along the edge of the brook, where it was warm and moist and delightfully sticky and oozy.”任溶溶的譯文是:“因此,當兩個朋友游泳、玩耍、用水你潑我我潑你時,威爾伯就待在河邊的爛泥里自得其樂,爛泥暖和,濕答答的,黏黏糊糊,舒服極了。”任溶溶選用兒童喜愛的疊詞和口語來譯,讀起來絲毫不“隔”,好像是中國作家原創(chuàng)的作品,真正做到了用中國話把外國作家的書講給中國小讀者聽。
這些譯文之所以獨具韻味,有時候并非只是憑借翻譯技巧,而是基于任溶溶本人多年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受翻譯蘇聯(lián)兒童文學作品影響,任溶溶自20世紀50年代起,即開始創(chuàng)作童話和兒童詩,發(fā)表了《沒頭腦和不高興》《一個天才雜技演員》等童話,及《我給小雞起名字》《一個怪物和一個小學生》等詩作。翻譯讓他了解、熟悉了外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作品的敘述技巧和藝術(shù)范式,為創(chuàng)作提供了借鑒;而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又讓他擁有了不俗的藝術(shù)判斷力和感知力,能夠更好地揣摩作家的心理,體悟中外語言表達的特點,從而將譯作更好地呈現(xiàn)。當然,這也和他本人對于翻譯的精益求精密不可分。任溶溶的譯稿通常寫在稿紙上,很多頁面涂滿了修改符號,因為在不同時間進行了反復修改,稿紙上經(jīng)常各色筆跡混雜。為了核實原著中的某一說法,他還經(jīng)常一遍又一遍地查閱各種資料,反復斟酌,直到自己滿意為止。在生活中,他也忘不了翻譯工作。有一次,他去外地開會,散會后特意去一家進口超市購買了一些零食,為的就是嘗一嘗他要翻譯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里提到的那些零食的滋味,以加深對原作的理解,更準確地翻譯。
除了譯作,任溶溶還撰寫了幾十篇翻譯批評文章,它們多以譯者序或譯后記的形式呈現(xiàn)。這些文章介紹了原作的社會文化背景、作家創(chuàng)作的整體狀況及譯者個人的翻譯心得,比較平實客觀。作為文學作品的副文本,這些譯者序、譯后記對于讀者深入理解譯作起到了指點迷津的作用,而且具有學術(shù)價值。
/結(jié)語/
任溶溶在創(chuàng)作、翻譯、編輯、文學批評四個領(lǐng)域都有獨特貢獻,是兒童文學界的一位通才。其中,“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無疑是任先生在漫長的文學歲月中投入心力最巨,累積成果最豐,介入人們的閱讀生活和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歷史發(fā)展十分廣袤、深邃的一個部分”(方衛(wèi)平《任溶溶譯文集·序言》)。
任溶溶一生翻譯出版三四百本作品,靠的不僅是才華,更多的是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及為中國兒童譯介好作品的使命感。任溶溶不是專職譯者,他的本職工作是編輯。因為編輯業(yè)務繁忙,他往往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時間,“一張紙,一支筆,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一頁一頁‘爬格子’”(任溶溶之子任容康語)。可以說,如果沒有任溶溶幾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大花園將遜色許多。
百歲人生,八十年筆耕;一腔熱血,全心為兒童。任溶溶的人格風范將和他的作品一起,繼續(xù)照亮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的前行之路。
本版照片選自《任溶溶譯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