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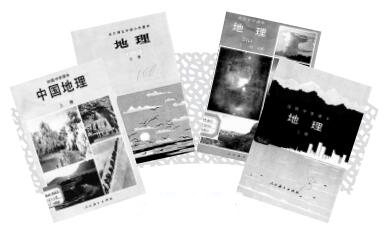
馬宗堯編繪的部分地理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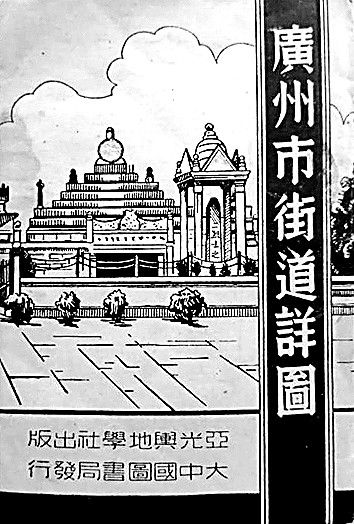
馬宗堯20世紀40年代編繪的《廣州市街道詳圖》。
學人小傳
馬宗堯(1917—2016),浙江海鹽人。地圖繪制專家,新中國地理教材地圖編繪的奠基人。早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學繪圖,歷任中華輿地學社繪圖員、海鹽玫瑰小學和思高中學教員、亞光輿地學社和中國史地學社編輯,繪制了許多中外地圖、地理教科圖及大城市圖、專題圖。自新中國成立到2000年,主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是前九套全國通用地理教材地圖的主要繪制者,撰有《對繪制地理課本附圖工作的一些體會》《我給課本繪地圖》等文章。
“說到新中國第一圖,就要提到它的編制者:馬宗堯。如果不是搞地圖收藏的,很少會有人知道馬宗堯這個名字,在中國地圖界他確實是一個非常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這是一位地圖收藏家寫下的話。其中說的“新中國第一圖”,指的是馬宗堯編制、中國史地學社1949年9月初版的《新中國地圖》和當年11月再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地圖》。
新中國成立之前,馬宗堯在上海任職于多家地圖社。自1950年到2000年,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整整50年。他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張全國地圖的編制者,又是新中國前九套全國通用課本地圖的主要繪制者,為我國地圖編繪和地理教材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回望其百年人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普通知識分子不平凡的人生之路和職業情懷,也可以窺見20世紀我國地圖繪制與地理教材的演變軌跡和發展歷程。
第二代地圖專家
馬宗堯,原名馬忠耀,1917年12月1日生于浙江海鹽。小時候,他跟祖父識字讀書,8歲入海寧袁花小學上學。其父馬紹良是我國第一代地圖繪制專家,任職于商務印書館輿地部多年,與葉圣陶、金仲華等交誼較深,著有《發電機電動機構造法》《理化簡易器械制作及實驗法》《法蘭西小史》等書。1929年,馬宗堯隨父遷居上海,轉學于商務印書館子弟校——尚公學校,老師余之介對他影響較大。此后,馬宗堯又就學于上海同義中學、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晚上和最要好的同學葛志成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夜校一起補習英文。
1936年,因家境有變,馬宗堯沒有繼續升學,跟著父親及其同事章志云學繪圖,后又師從于馮賓符、金仲華,邊學邊干,還在進步刊物《譯報周刊》和《世界知識》擔任時事地圖欄目的繪圖員。在舊中國,沒有專門培養制圖人員的學校,從業者全靠在工作實踐中傳、幫、帶。當時的商務印書館既是全國最大的出版機構,也是一個擁有眾多專家的學術高地,其中匯集了一批地圖專業人才,“使地圖的出版在質量、數量等方面,都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在地圖編制和培養制圖人才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馬宗堯就是商務印書館“培養出的第二代地圖專家”之一。(陳潮《商務印書館與地圖出版》)其間,在師傅帶領下,馬宗堯與陸承蔭、陸先鑒等一起切磋繪圖技術,勤學苦練,逐漸對這個行當產生了濃厚興趣。他曾回憶說,一方面自學《地圖學》《實用地理學》《地圖投影學》等書,奠定了理論知識基礎;另一方面鉆研《申報》地圖與外文的古氏地圖、牛津地圖、菲律普袖珍地圖的編繪方法,他掌握了一些先進的地圖繪制法。筆者查閱文獻,發現馬宗堯最早手繪的四幅作品,即《太平洋軍略現勢圖》(1939年)、《英倫三島的障壁:七道堅強防御線圖》(1940年)、《危機四伏中的巴爾干形勢圖》(1940年)、《協約國對德經濟封鎖圖》(1940年),均署名“馬忠耀”,分別發表在《譯報周刊》《世界畫報》《時代》《世界知識》雜志上。
1940年,馬宗堯應聘在中華輿地學社擔任繪圖員,并參與地圖制版、印刷和出版工作,從而了解和掌握了地圖編輯出版的全流程。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上海租界,出版界一片凋零,中華輿地學社宣告解散,馬宗堯失業,從上海逃回家鄉海鹽,在石泉鎮玫瑰小學擔任美術教員,又在其初中補習班(后改為思高中學)教數學、地理。(馬宗堯《石泉玫瑰小學》)在家鄉,馬宗堯與其他老師以學校為掩護,進行抗日救國教育,抵制日偽奴化教育。(宋立宏《抗日戰爭時期的海鹽教育》)
抗戰勝利后,馬宗堯重回上海,經好友陸承蔭介紹,任職于亞光輿地學社(以下簡稱“亞光”)。這是由金振宇、金緯宇、金擎宇兄弟三人于1938年秋在上海合資設立的一家地圖出版機構。1942年“亞光”在重慶與著名史地學者顧頡剛、李承三共同創建“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顧頡剛、李承三分別擔任正、副社長,金擎宇為總干事。同年,他們又合伙成立“大中國圖書局”,由顧頡剛擔任總經理兼編輯所所長。這三家機構一個負責編輯,一個負責出版,一個負責發行,相輔相成,雖然相對獨立,但實際上由“亞光”主導。其老板善于經營,發展很快。1945年遷滬后,“亞光”還創設專門印刷地圖的彩印廠和匯集各種地圖的資料室,從而形成了編繪、制版、印刷、發行全部工序一條龍,幾年工夫就成為業界佼佼者,到新中國成立之初已發展成為國內最有名的一家專業地圖出版社。金擎宇回憶說,“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多時間里,我們出版的新圖已達五十多種。在編繪力量上先后增加了凌大夏、張家駒、馬宗堯、劉思源、董石聲、盧綿高等同志。他們都是編繪能手,又富于經驗,對我社地圖質量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而且“后來都成為地圖事業上各方面的領導和骨干力量”。(金擎宇《記亞光輿地學社的創設與發展》)在“亞光”,馬宗堯開啟了地理教科書繪圖事業,也迎來了地圖繪制工作的一段“高光時刻”。他既參與了《中國地理教科圖》(1946年)、《世界地理教科圖》(1947年)等課本地圖的繪制,又負責編制了一些中外地圖和城市地圖,如《南京市街道詳圖》(1946年)、《廣州市街道詳圖》(1948年)、《上海市街道詳圖》(1948年)、《最新世界大地圖》(1949年)、《最新世界分國精圖》(1949年)等。其中,《最新世界大地圖》為單幅大掛圖,印了十多版。根據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圖書期刊司發布的《1950年全國新書目》,在“地圖”類別中,“亞光”出版的地圖品種最多(約40種),占一半份額,其他由新華、中華、商務、復興、新亞、亞新、震球、三聯、大中國、世界知識、史地學社等出版。其中,署名“馬宗堯”的地圖作品一共有9項。
編制“新中國第一圖”
1949年2月,馬宗堯與同事凌大夏等合伙成立“中國史地學社”(后改名為“華夏史地學社”),并趕制了《上海市里弄詳圖》《簡明中國地圖》《簡明世界地圖》《新中國地圖》《新世界地圖》《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地圖》等,銷路很好。他們很注意切合社會需要,根據國家形勢尤其是戰事局勢變化,不斷修訂再版,不僅使“中國史地學社”得以保存下來,而且也使馬宗堯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張全國地圖的編制者。
這幅地圖最早叫《新中國地圖》,于1949年9月出版,單幅三套色,縱76厘米,橫54厘米,不大也不小。收有此圖的宗緒盛說:“圖的左框外印有‘編制者:馬宗堯’‘發行者:中國史地學社’。”“這是一幅乍一看十分普通的民國地圖,卻是筆者多年收藏至今所能見到的唯一一幅‘最早’真實記錄和見證了國民黨統治下的中華民國的垮臺和新中國的誕生,并以最快捷的速度透露和記載了北平被重新改名為‘北京’、成為新中國首都這一歷史信息的珍稀地圖。”(宗緒盛《老北京地圖的記憶》)這幅地圖根據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用套紅方式標出當時“解放區”(東北、華北、華東、西北、華中、瓊崖)和“待解放區”(西南、臺灣)的分布情況,說明國民黨反動統治已基本被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條件已經成熟。而且,此圖還明確繪制和標示了東海及南海諸島,并把“曾母灘”即曾母暗沙作為祖國南疆的最南端,即把最南的范圍線止于此處,以此表明自古以來這就是中國神圣領土的組成部分,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上的鮮明立場和態度。《新中國地圖》能夠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趕制出來,是給開國大典的一份獻禮,也是新中國誕生的見證。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國家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9月27日,又作出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國旗、國歌、紀年4個重要決議,決定以北平為首都并改名為“北京”,采用公元紀年等。據此,馬宗堯對《新中國地圖》進行修訂完善,并將圖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地圖》,于1949年11月由中國史地學社再版發行。因此,嚴格說來,這張三色單幅地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中國第一圖”,之前的《新中國地圖》應該叫做“新中國解放圖”。這兩幅地圖在我國地圖史上都具有開創性意義。馬宗堯能夠與時俱進,先后及時繪出最新全國地圖,很有遠見,難能可貴。據說,同時“亞光”也在趕制《新中國大地圖》,但1950年1月才出版。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50年年初,馬宗堯還應《人民中國》英文半月刊之邀繪制了一些地圖,其中一幅是“Ma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也是三套色地圖。這是我國最早用外文向國外推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其歷史意義也不可小覷。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當年7月31日,馬宗堯及時繪完《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形勢圖》(單幅黑白圖)。這幅刊于1950年8月號《新華月報》的地圖,從地圖視角及時反映當時的戰爭態勢,為后來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增了磚、添了瓦。
編繪新中國課本地圖
說起新中國課本地圖的繪圖,馬宗堯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設立編審局,由副署長葉圣陶兼任局長,負責教科用書、一般圖書及地圖、辭書等編制工作。經金仲華介紹,馬宗堯調到編審局教科書編審處史地組任繪圖編輯。對此,《葉圣陶日記》多有記載:
1949年10月27日 大中國書局三位(編者按,指金擎宇、馬宗堯、凌大夏)來,言高小地理中地圖太不成樣子,愿意為之重繪。其意甚可感,即決定重繪。
1950年3月1日 馬宗堯君始入局工作。馬之父紹良,系余前在商務時之同事,繪地圖。宗堯傳其父業。我局須繪圖于教本,故余招之。
1950年4月17日 地理組開組會,討論工作計劃。所需新編中學地理書凡五種,其一半將約社外人士編之。又繪制小學之地圖,由馬宗堯、侯峙二人動手。
自此,馬宗堯開啟了后半生長達50年的教材地圖編繪事業。那時,他繪圖的《初中本國地理課本》(曾次亮編)、《高中自然地理課本》(田世英編)等教科書,均由新華書店出版發行。
1950年12月,在編審局基礎上成立了人教社編審部,馬宗堯轉到該社地理編輯室工作,并加入了九三學社。在室主任田世英、葉立群、陳爾壽等先后領導下,他參與了人教版前九套地理教材繪圖的所有工作。其中,“文革”前有四套,改革開放至新世紀之前有五套,馬宗堯因此成為新中國統編教材地圖編繪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
這里僅以第一套、第二套教材(1951年—1957年)為例。由馬宗堯繪圖的地理教材,除了修訂再版的《高中自然地理課本》《初中本國地理課本》之外,還有《高中本國地理課本》(田世英、鄧啟東編)、《人民民主國家地理》(周光歧編)、《高中課本外國經濟地理》與《初中課本世界地理》(顏廼卿、周光歧編)、《初中課本中國地理》(王鈞衡、田世英編)、《中學外國地理暗射地圖》(與侯峙合作)、《高小課本地理》(陳爾壽等編)、《業余學校課本地理》(李藝莊編)、《工農速成中學課本世界地理》(顏廼卿等編)、《工農業余初中地理》(何惠生編)、《高中課本中國經濟地理教學參考書》(葉立群、陳爾壽等編)、《師范學校課本地理》(芮喬松、李明編)、《師范學校課本中國地理》(厲鼎勛、田世英等編)、《師范學校課本外國地理》(顏廼卿、周光歧編),以及未署名的兩套高小地理課本等。此外,他還為部分歷史教材繪制了地圖,如《初中課本中國歷史》(李賡續編)、《高中課本中國近代史》(王芝九編)等。
1956年8月,馬宗堯在人教社內刊《編輯工作》發表《對繪制地理課本附圖工作的一些體會》。他說,“幾年來,我在實際工作和學習中認識到課本附圖的重要性”,“地圖是地理教學中最重要的直觀教具,能幫助學生了解和記憶地理教材的內容”,雖然“課本附圖要按照課本開本的大小,在很小的紙面上繪出很大的區域來,內容要比一般參考地圖簡單得多”,但是“地圖是課本不能缺少的組成部分,對質量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特別是“我們編輯出版的課本供應全國所有中小學,影響全國幾千萬學生,課本的附圖,無論內容或繪制技巧都要是正確的、進步的”。通過學習國外課本制圖方法、向地圖出版社請教等,“現在地理課本的附圖比三四年前有了不少改進,大體上做到地圖能密切配合課文的內容,并反映國家建設的發展”。他總結自己的經驗,“大致說來,一定要繪出跟課文有關的材料。小學和初中課本的附圖要用粗線條表示,圖上的符號要突出、醒目,才能引起學生看地圖的興趣。高中課本的附圖要繪得比較細致,內容可以復雜一些”。
1958年以后,中學地理改為兩門,小學地理減少課時。相應地,課本進行了重編,大部分地圖也進行了重制。這是新中國第三套教材。1962年,新編十二年學制的中國地理課本開始編寫,對課本地圖又提出了高要求。為此,馬宗堯與從地圖出版社借調的兩位繪圖者,在學習文件和國外地理課本最新制圖經驗的基礎上,一起編繪了新中國第四套地理教材。這也是教材內容和繪圖質量都很高的一套教材。此外,他還為《蘇聯大百科全書·美洲卷》繪制了“北美洲行政區劃圖”(1956年),為《我國的南海諸島》一書繪制了“南海諸島圖”(1962年)。
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
“文革”期間,馬宗堯到“五七干校”勞動。1978年,年過六旬的馬宗堯重新歸隊,再次全身心投入地理教材的編繪工作。從1978年到2000年,他直接參與繪圖的全國統編或通用的中小學地理教材,總計有五套、30多種、近百冊。其中,既有十年制、十二年制的初、高中教材,也有五年制小學和義務教育教材,還有職業高中、成人高中、職工業余中學、中等師范、幼兒師范以及衛星電視教育教師培訓教材;既有早期的“試用本”,又有后來修訂完善的“正式本”和改革探索的“試驗本”;既有高中必修課本及其教參,也有高中選修課本及其教參;既有地理課本插圖,也有地圖冊和分幅地圖等。
馬宗堯回憶說:“課本地圖的編繪方法靠的是不斷摸索,在工作中學習。”“從1950年12月到2000年,人教社已出版九套教材,地理課本的地圖也一步步改進。現在回想起來,其中有很多艱難險阻……課本地圖看起來很簡單,實際的工作程序是很煩瑣的。”(馬宗堯《我給課本繪地圖》)
比如,1978年人教社出版的十年制初中試用課本《中國地理》《世界地理》及其教參,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套統編地理教材,也是新中國第五套地理教材。當時遇到的困難,一方面是幾本書同時編,時間緊、人力少;另一方面是中外地圖的繪制都面臨很大挑戰。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此時的行政區劃與十幾年前發生了許多變化,我國先后與大部分周邊國家簽訂了邊界條約,要求課本地圖進行相應調整和更新。同時,世界地圖的發展變化也很大,其間許多殖民國家地區相繼取得獨立,我國也已跟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外交關系,這些都要在世界地圖上反映出來。為此,馬宗堯帶著助手們全力投入,徹夜奮戰,加班加點,順利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保證了新課本的地圖質量。
鑒于當時地圖繪制和印刷技術都有新的進展,即由過去的鋅版單色地圖逐步改為膠版彩色地圖,馬宗堯老當益壯,邊干邊學,仔細鉆研國外地理教科書,琢磨其地圖繪制的新觀念新方法。在1981年版《全日制五年制小學課本地理(試用本)》中,他采用了細線條較多的繪制方式,增繪了四張彩色地圖插頁。此書制印質量優良,實現了新突破。此外,馬宗堯還為1983年初版的《新編小學生字典》繪制了中國政區圖和南海諸島圖。
為1982年版《高中課本地理(試用本)》(陳爾壽主編)繪制地圖的工作,是最難啃的骨頭。因為這本教材需要繪制各種世界專題地圖,像氣候、自然帶、洋流、土壤、石油、煤鐵、經濟作物、森林、人口等專題地圖,又沒有現成對應的世界地圖可供采用,馬宗堯參考了很多資料,如國外最新出版的古氏世界地圖、蘇聯教師地圖、法國普通世界地圖、西德韋特斯曼學校地圖,還有美國的世界自然地理地圖、日本中學地理課本中的世界地圖,以及國內的大學地理教材等。但在繪制過程中,他又遇到了一個新問題,即外文世界地圖有各種不同的地圖投影,圖幅較大,編繪適合高中地理課本使用的世界專題地圖,必須把這些地圖經過選擇、簡化、縮小,并轉繪到我國常用的“等差分緯線多圓錐投影”的世界地圖上。此外,這個課本中中國地圖有10張專題圖,當時有公開出版、內容較新的中國地圖作依據,但要繪制適合課本大小的中國地圖,就要把參考地圖的內容簡化、縮小并轉繪到中國輪廓圖上。為了完成上述多項艱巨任務,配合教材內容做好地圖編繪工作,馬宗堯竭盡全力,付出許多心血和智慧。由于這部教材地圖編繪比較規范、資料數據可靠,并通過權威部門審查,所以不少地圖常為社會地理書刊所采用、引用和借用。該教材在1985年、1990年先后兩次修訂再版為《高中課本地理》,馬宗堯又分別做了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在他看來,“地理課本是為全國各大中小學服務,意義非常重大,不允許有任何閃失”(馬宗堯《我給課本繪地圖》)。
2000年,83歲的馬宗堯從工作崗位徹底退了下來,他為新中國教材地圖事業奮斗了半個世紀,影響了幾代學子,為提高我國中小學地理學科水平、增強青少年中外地理素養作出了重要貢獻。正如其名,馬宗堯就像一匹馳騁的駿馬,尊崇堯舜之道,忠于制圖之業,即便老驥伏櫪,仍志在千里。可以說,無論是在新中國還是在舊社會,專業從事課本地圖繪制工作,并且干了這么長時間的,再也找不出第二位。這種獨一無二的特殊貢獻,這種少見的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的能耐,怎能不讓人感慨。
退休之后,馬老曾說:“從1950年12月到2000年,我在人教社地理室工作了近五十個春秋……現在我每天打拳、練劍、看報、讀雜志,并搜集地圖方面的信息,將其視為晚年平靜生活的樂趣。”(馬宗堯《我給課本繪地圖》)看來,晚年的馬老并沒有完全閑下來,他一方面關心家鄉海鹽的建設和發展,并應當地文史資料征集部門的請求,撰寫了一些回憶錄,另一方面更多地延續多年的工作習慣,繼續收集地圖資料,不時詢問新教材繪圖的進展情況,還撰寫一些文章總結半個多世紀編繪課本地圖的經驗。在一份工作總結中,他提出了對課本繪圖的基本觀點:首先,要保證地圖不出政治問題。這既是地圖的特點決定的,也取決于教材的特殊性。其次,要重視地圖資料的來源。對引用的各種地圖資料要分析、選擇,并考慮到地理課本的需要而取舍。要不斷更新,使地圖繪制所擬采用的資料跟上形勢的發展。如果繪制某些地圖資料不足,可把地圖送有關業務部門審查,請其提出修改意見或供給資料,以確保課本地圖的科學性。再次,要認識課本地圖的特點。課本地圖是小比例地圖,一幅地圖只表示課文內容所述及的一兩個問題,繪制內容要進行較大的簡化、綜合,做到圖文一致,圖面清晰,重點突出,容易閱讀,便于教學,尤其是有利于學生運用地圖分析課文,幫助學生理解和記憶地理課上學到的有關知識。
2016年,馬宗堯在京逝世,享年100歲。他走過了風云變幻的一個世紀,留下了深深的足跡。
本版圖片由馬宗堯女兒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