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六朝的《春秋》學與文學研究”負責人、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詳細探討了六朝的志怪,當論及顏之推《冤魂志》時,云其“引經史以證報應,已開混合儒釋之端矣”。這一論斷表明,魯迅已經意識到六朝志怪與儒家經典之間存在聯系。六朝時期,儒家經典是士人知識體系的重要基礎,士人的創作受到經傳影響頗深。干寶在編纂《搜神記》時即取法《春秋》經傳,從內容形式到思想旨歸,皆與《春秋》經傳密不可分。
《春秋》“義例”對《搜神記》的影響
漢唐間學術格局的轉型,實際上就是圍繞經史關系展開的。在這一時期士人的觀念中,《春秋》及其三傳不僅是儒家經典,更是史家著述的典范。所以自魏晉起,史家又開始重視編年體,如習鑿齒《漢晉春秋》、孫盛《魏氏春秋》及孔舒元《漢魏春秋》等,這些著述從命名到體例都取法《春秋》。
這成為一時之風尚,而引領者正是干寶。干寶對歷代史家多有批評卻唯獨褒揚《左傳》,在討論《晉史》撰寫時也力主以左丘明為標準。他本人也為《春秋》做過注疏,可知的有《春秋左氏義外傳》《春秋左傳函傳義》與《春秋序論》。干寶的《晉紀》有“良史”的美譽,這是他仿效《左傳》修撰的。他著述《搜神記》,實際上也受到了《春秋》經傳的影響。
干寶《搜神記》被《隋書·經籍志》歸入“史部”,漢唐人皆視其為史書。據逯耀東統計,有十五部史書征引了《搜神記》的材料,可以說《搜神記》本為史著的性質是毋庸置疑的。干寶編修《搜神記》“非有意為小說”,而是以史家身份搜輯舊聞,取法《春秋》經傳,旨在“明神道之不誣也”。
《春秋》經傳對《搜神記》的滲透是多方面的,最顯著的就是《春秋》“義例”之學的影響。所謂“義例”,概略而言指的是“微言大義”與“書法”“條例”,《春秋》所蘊含的“義”又是寓于“例”的。比如說“鄭伯克段于鄢”,不稱“公”而書“伯”,不言“公子段”而書“段”,即貶義,斥其有違人倫。干寶在撰《晉紀》時所立“史例”也是《春秋》“義例”之學影響的結果。劉知幾《史通》對此有高度評價:“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搜神記》實際上也受到了《春秋》“義例”之學的影響,如果細致研讀《搜神記》的文本,可以在諸多細節之處尋繹到這種影響的痕跡。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詩》有美刺而《春秋》寓褒貶,二者都寄寓著價值評判。《春秋》旨在“勸善懲惡”,這一“大義”由司馬遷著史而鞏固,在干寶的著作中得到發揚。干寶著《晉紀》,激烈抨擊了西晉善惡不分、毀譽無當的現實,對道德禮法的傾頹深感痛心,表現出強烈的儒家價值立場。《搜神記》記述的許多事跡意在表彰儒家道德禮法,其敘事往往借助感應學說。比如,王祥侍奉繼母,繼母冬天欲食魚,又思黃雀炙,二物皆自投羅網,這是王祥孝感所致。郭巨欲埋兒存母,上天感其孝心賜金一釜。這些故事顯然反映了“人道”與“天道”間的感應關系,指向了善惡有報的觀念,是《春秋》“善善惡惡”的大義所在。
《搜神記》與其他志怪存在一個顯著的不同,是書中許多故事的紀時十分明確。如“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后梁氏誅滅”。這里的敘事既有年月又有時節,實際上是史家修史之法,其根源乃在《春秋》“書法”。
《春秋》紀時遵循“日月時”例,古代學者相信《春秋》記事所書時節、月與日都有著嚴格的原則。《谷梁傳集解》云:“凡年首,月承于時,時承于年。”年居于首,其次書時節,再書月,最末書日。根據記載事件內容、性質、程度等差異,有的記載到年,有的書到時節,有的具體到日。在古代的學者看來,《春秋》這樣的書法寄寓了圣人的褒貶與“微言大義”。《春秋》載:“夏,五月,莒人入向。”范寧認為,入侵之事慣例是書時節,事極惡書日,次一等書月,所以此處書月隱含了圣人的貶義。《搜神記》中數次言及王莽篡政時都是書月,而說到曹魏代漢、晉室興起也一律書月,這些表明干寶的書寫繼承了《春秋》書事的體例,暗寓了“微言大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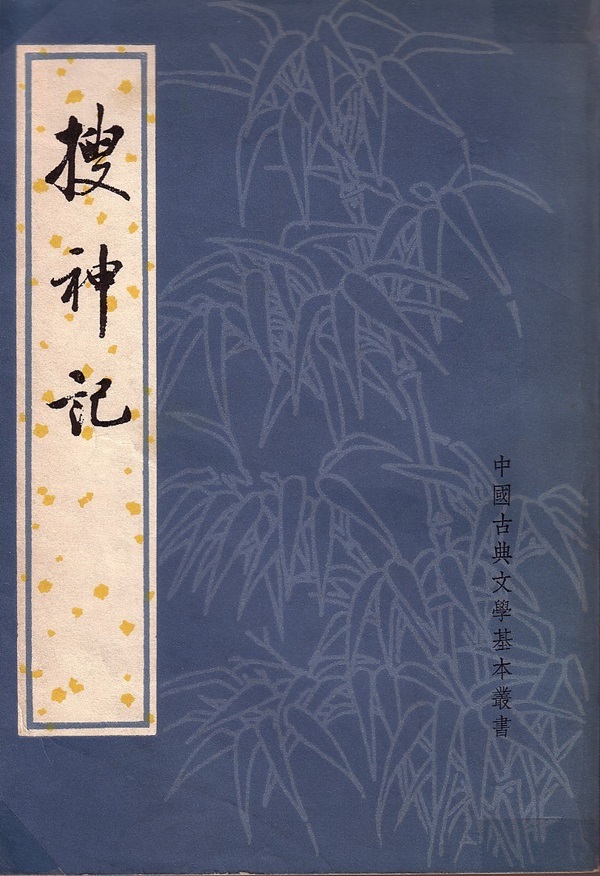
《搜神記》書影 資料圖片
《春秋》經傳與《搜神記》的敘事
《搜神記》以《春秋》經傳為范本,在敘事上表現得比較明顯。我們可以發現《搜神記》許多故事都脫胎于《春秋》經傳。《左傳》中記載了莊公十四年鄭國兩蛇相斗之事,《搜神記》也迻錄此事,并引京房《易傳》之說將此事與立嗣勾連起來加以解釋。干寶又以兩蛇相斗這一敘事模型講述漢武帝巫蠱之禍:“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斗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搜神記》中鬼魂復仇索命的故事也本于《左傳》。《左傳》載晉侯夢厲鬼,言晉侯殺其孫乃是不義,故上訴天帝為其孫復仇,晉侯不久果然沒有逃脫死亡的命運。干寶在《搜神記》中復制了這一故事情節,漢靈帝夢到桓帝,桓帝斥責他聽信邪佞害死了宋皇后與渤海王,二人上訴天帝,后靈帝驚恐不已,不久便死去。《春秋》經傳的這類復仇故事,經《搜神記》的演繹,發展為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一個重要母題。
《搜神記》以異象展開預言的敘事方式更是與《春秋》經傳如出一轍。《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就認為數年內有大禍,幾乎到了亡國之境地。次年韓原之戰,晉惠公被秦軍俘虜,是為應驗。《搜神記》:“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鷇于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于是認為這是事關曹魏宮室的異象,應當防范權臣禍起蕭墻。這一敘事模式與《左傳》相同,先書時間,次述異象,再借他人之口加以解釋,道出預言。
干寶敘事頗為人詬病的是《搜神記》所記“怪力亂神”之事,從表面看來這有違儒家的教訓,但是從引入《春秋》經傳的角度來觀察,我們就會有新的認識。事實上,干寶屬意于神異之事并非他嗜奇,而是要從中尋找出治亂之道,其基本的思維方式乃是沿著董仲舒、何休等《春秋》學家而來。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董仲舒認為,所有災異之象,根本就在于國家有失,上天通過異象來示警。何休的意見與董仲舒頗為相近,他們通過對《春秋》經傳的解讀,建立起天人感應學說。天道與人事息息相關,國家政治有失,上天即以災異示警,這就是天人配合的感應說。正是遵循這一思路,干寶敘事重神異,旨在關注現實,寄寓其態度。
《搜神記》記載了漢元帝時期官吏伐斷大槐樹,而后槐樹又復生,干寶援引今文經說以為這是劉秀中興的征兆。又一則講述了漢哀帝時汝南一地樹木長成人形,干寶便征引京房《易傳》加以解釋,認為這是“王德欲衰,下人將起”之故,并將此異事與王莽篡政對應起來。在涉及兩晉歷史之處,他仍舊將現實政治置于天人感應的解釋框架中加以敘說。晉惠帝元康年間,天雷擊破宮中求嗣的高禖石,干寶視其為賈后之誅的先兆。晉元帝太興元年地震山崩,干寶便以此附會現實,認為這是王敦以下凌上的征兆。這些敘事暗含了作者的褒貶取向,借由天人感應學說,賦予了作者揭示、批評現實的敘事合法性。
有時候,干寶將“天道”具體化,他認為天有五氣,萬物化成,因而常以“氣”來解釋人事與天道的關系,“氣”變亂無常而導致異象出現。例如,《搜神記》中記載的“蜮”,《春秋》亦有此物,《公羊傳》云“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干寶進一步提出,“先儒以為南方男女同川而浴,亂氣之所生也”,這一解釋仍舊屬漢代公羊學的看法。
《搜神記》取法《春秋》經傳的用意與意義
那么,干寶為何要“擬經”,取法《春秋》經傳的深層用意何在?我們可以認為,《春秋》經傳既為《搜神記》的創作提供了知識性的素材,又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其符合儒家思想的規范。
《搜神記》中相當一部分故事的來源就是《春秋》經傳,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經書與傳注,漢代盛行的緯書也是其寫作的重要材料。所謂緯書,是相對于經書而言,可以看作經書的衍生品,漢人將其視為經學的一部分。干寶在其志怪小說的寫作中吸收了不少讖緯材料,如“慶都”條:“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這條記述完全就是對緯書《春秋合誠圖》內容的簡化,《春秋》經傳為其提供了創作的素材,成為干寶整個知識系統的來源之一。
更為重要的是,《春秋》經傳為《搜神記》的書寫提供了合法性。魏晉時期,儒學對社會的規制作用不如漢代那樣強大,但這并不意味著儒學失去了影響力。實際上,六朝士族與儒學交織在一起,不可分割。干寶的思想底色就是儒學,他在《搜神記》的序言中提及《春秋》與《史記》:“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春秋》二傳紀事尚且無法做到“無失實者”,他又繼續為自己的著述辯解,在他看來,《搜神記》輯錄的一些故事雖然荒誕不經,卻是前代經典所載。至于那些近世之事,如有虛妄,也是效法先賢前儒。從干寶自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的意圖,通過依經,《搜神記》中看似荒誕虛妄的內容便不再是離經叛道,那些神異敘事便有了存在的合法性。
兩漢以降的經學地位尊崇,構成了古代士人知識體系的基礎,是古代思想理論建構的重要資源。六朝敘事文體或顯或隱地受到了經學的影響,無論是形式內容還是思想宗旨,都不同程度呈現出“擬經”的面目。從《春秋》經傳與《搜神記》的文本關系來看,六朝敘事中諸多現象看似離經叛道,但細究之下可以訝異地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天然的深刻聯系。六朝敘事文學的發展演變確受儒家經典的沾溉,經傳作為六朝敘事文學淵源之一的地位不言而喻。發掘《春秋》經傳與干寶《搜神記》之間深刻幽微的文本關系,有助于提示我們透過文本去體察作品背后深邃的思想世界,更讓我們認識到儒家經典與文學文本間存在的復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