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培成,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锳

王锳(左)與學生交流。

王锳(左三)與學生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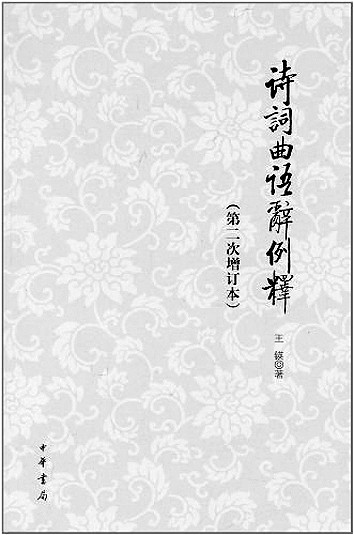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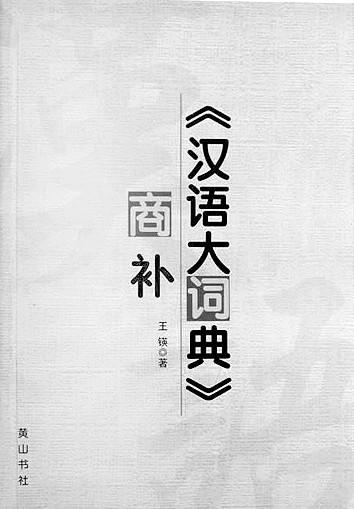
學人小傳
王锳(1933—2015),四川成都人。語言學家。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2年畢業,先后任教于北京師范專科學校、遵義師范專科學校、遵義教育學院、貴州民族學院、貴州大學。曾兼任貴州省語言學會會長。著有《詩詞曲語辭例釋》《唐宋筆記語辭匯釋》《宋元明市語匯釋》《〈漢語大詞典〉商補》《〈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等。
學界新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8年時間,我和王锳的人生軌跡基本重合,我們也因此成為摯友。
王锳193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參軍,參加過川藏公路雀兒山段的建設。1957年,王锳和我都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為同學,1959年又一起被分入語言專門化。1962年本科畢業,我們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由教育局再分配到北京師范專科學校教授古代漢語課。我和他同住一間寢室,朝夕相見。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要講授古代漢語這樣重要的基礎課,談何容易。我們認真備課,爭取老教師的指導。那時王锳已經結婚,愛人在貴陽工作。1965年,北京師范專科學校停辦,王锳去貴州與妻子團聚,我被分到北京女八中做語文教師。
“文革”結束后,《中國語文》雜志復刊,王锳向該刊投稿。京黔兩地相距遙遠,當時通信不便,他委托我為代理人,稿件如有問題,我可以代他與編輯部商討處理。這篇文章就是1978年第3期《中國語文》刊發的《詩詞曲語辭舉例》,受到語言學界的重視,其中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呂叔湘先生、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朱德熙先生這兩位著名語言學家。
1983年春,呂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克服種種困難,邀請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梅祖麟到北大中文系開設語法史專題課,目的是要推動國內的近代漢語研究。在講座開始前,呂先生和朱先生想到了王锳。王锳雖然是北大中文系的畢業生,但是呂、朱對他并不熟悉,給他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王锳發表在《中國語文》上的那篇論文。他們認為王锳是可以造就的人才,愿意盡可能為他提供深造的機會。王锳當時在貴州的一所師范學院任教,要他自己申請離開工作崗位半年到北大進修,還要自己承擔費用,是很大的難題。呂、朱二位沒有放棄努力,經過協調,北大中文系發函聘請王锳到北大講學,由北大承擔食宿等費用。接到聘書后,王锳整裝進京,重返燕園。不過他不是來講學,而是來聽梅祖麟的課程。在那段時間,王锳還跟隨呂、朱兩位先生去太原參加全國語言學學科工作規劃會議,開闊了眼界。
勝義紛呈的《例釋》
王锳在語言文字方面的著作,我見到的有十幾種,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詩詞曲語辭例釋》。
在《詩詞曲語辭例釋》之前,近代學者張相撰寫過《詩詞曲語辭匯釋》。所謂“詩詞曲語辭”,按照張相先生的說法,“約當唐宋金元明間,流行于詩詞曲之特殊語辭,自單字以至短語,其性質泰半通俗,非雅詁舊義所能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習見也”。“詩詞曲語辭”實際上就是唐宋以降漢語口語中的新詞新義。由于歷史原因,傳統訓詁學研究的重點是先秦兩漢的“雅詁舊義”,對唐宋以下近代漢語階段口語詞匯則很少問津。這不僅造成了漢語詞匯史研究的大段空白,也影響到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古籍整理,以及對這一漫長歷史階段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
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突破了傳統訓詁學取材的狹隘范圍,注意到唐以后保存口語資料較多的詩詞劇曲,開辟了語言研究的新領域。不過因為這項工作具有開拓性,《匯釋》在收詞、釋義方面,難免有所失漏。王锳的《詩詞曲語辭例釋》意在補充《匯釋》的不足,搜集并詮釋其失收的條目,完善或修正其部分條目的釋義。在資料來源、取例匯義、編排體例、研究方法等方面,《例釋》大都能繼承《匯釋》的優點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改進。《例釋》于1980年由中華書局初版印行,產生廣泛影響。呂叔湘在給王锳的信中給予“探微索隱,甚見功力”的評語。北大教授蔣紹愚在《唐詩語言研究》中對《例釋》評價說:“在收羅宏富、釋義精確方面,此書繼承了《匯釋》的長處,但所謂補遺,則不僅是收列了《匯釋》中未收的條目,而且對《匯釋》已收條目詮釋不妥與遺漏之處也做了糾正和補充。更重要的是方法上比《匯釋》有所改進,首先是注意了詞義之間的聯系,其次是有了較明確的語法觀念……這是一部關于詩詞曲語辭研究的高水平著作。”由于學界的推許,該書于1987年獲首屆吳玉章獎金的語言文字學優秀獎。下面例舉《詩詞曲語辭例釋》(第二次增訂本)對《詩詞曲語辭匯釋》的兩處修正或補充。
如,《匯釋》卷五“辦”字條云:“有辦到義;有準備義;有具備義。”《例釋》:“‘辦’還經常用于主要動詞之前作助動詞,表示可能,義與‘能’同。在這種情況下已不能仍以‘辦到’等義為解。唐獨孤及《得李滁州書以玉潭莊見托因書春思以詩代答》:‘知同百口累,曷日辦抽簪?’意謂何日能退隱也。皮日休《奉和魯望秋日遣懷次韻》:‘破衲雖云補,閑齋未辦苫。’司空圖《白菊雜書》四首之三:‘侯印幾人封萬戶,儂家只辦買孤峰。’均猶言‘未能’‘只能’……另,‘辦’與‘得’均有‘能’義,二者往往連用,猶言‘能夠’。黃機《乳燕飛》詞:‘繡帽輕裘真男子,政何須、紙上分今古。未辦得,賦歸去。’程大昌《念奴嬌》詞:‘縱有知聞,誰辦得、駕野凌寒秉燭。’”再如,《匯釋》卷五“處分”條:“猶云吩咐或囑咐也,與本義之作處理解者異。”《例釋》:“除此之外,‘處分’在劇曲中還可表示‘責備’的意思,其程度較斥罵為輕。《竇娥冤》劇楔子:‘婆婆,端云孩兒該打呵,看小生面則罵幾句;當罵呵,則處分幾句。’《酷寒亭》劇一:‘大姐,孩兒癡頑,待打時你罵幾句,待罵時你處分咱!’二例顯然既非斥罵,又非一般的囑咐,而是‘責備幾句’‘說(他)幾句’的意思。《王西廂》三之三:‘怎想湖山邊,不記西廂下,香美娘處分破花木瓜。’也是指鶯鶯責備張生非禮。‘破’為‘了’‘著’義(見《匯釋》卷三該條)。《梧桐葉》劇一:‘(卜兒云)你題甚詩?(正旦唱)這詞又不是道春情子曰詩云,暗傷神,雨淚紛紛,低首無言聽處分。(卜兒云)雖然如此,你是女子,賡和他人詞章,是何體面?’義亦同。”可見,《例釋》對《匯釋》的修正或補充,是以豐富的文獻材料作為支撐的。
《例釋》不僅修正或補充《匯釋》已有的條目,而且增補了許多條目,豐富了詩詞曲條目。下面例舉兩條:
“更,與類連詞,與通常作副詞用者有別。皇甫冉《雜言月洲歌送趙冽還襄陽》詩:‘流聒聒兮湍與瀨,草青青兮春更秋。’‘與’‘更’互文。楊萬里《春興》詩:‘著盡工夫是化工,不關春雨更春風。’又《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絕句》:‘阿誰不識珠將玉,若個關渠風更騷。’‘更’‘將’互文,‘將’亦為‘與’字義。姜夔《卜算子》詞:‘綠萼更橫枝,多少梅花樣。’作者自注:‘綠萼、橫枝,皆梅別種。’辛棄疾《鷓鴣天》詞:‘攜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開。’余桂英《小桃紅》詞:‘早知人、酒病更詩愁,鎮輕隨飛絮。’石孝友《謁金門》詞:‘洞里小桃音信阻。幾番風更雨。’王質《水調歌頭》詞(京口):‘古戰場,盡白草,更荒煙。’其義并同。”
“輟,分給。李白《贈黃山胡公求白鷴》詩:‘我愿得此鳥,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輟贈,分贈或轉贈。韓愈《病鴟》詩:‘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貍。’陸龜蒙《奉酬襲美苦雨見寄》詩:‘唯君浩嘆非庸人,分衣輟飲來相親。’……義均同。由‘分給’義引申,‘輟’有時可徑作‘借’解。《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七《與朱行中舍人書》:‘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輟’‘借’連言,均表借義……以上‘輟’用于指稱物,如用于指稱人,則有‘分派’義。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詩:‘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卷五于此詩之‘輟’字下注:‘疑作綴。’按,此屬錯疑,蓋因不知‘輟’有分派義而然。首句倒裝,猶言‘輟諫官(與)幕府’,即分派諫官至幕府之意……按《說文·車部》:‘輟,車小缺復合者。’與車輛的行止有關,很難引申出分給義。‘輟’表分給義應是‘餟’的假借……《方言》卷十二:‘餟,饋也。’從饋贈義引申為分惠于人之義是順理成章的。”
蔣紹愚所論“注意了詞義之間的聯系”“有了較明確的語法觀念”從這些例子中可見一斑。
《商補》《續編》的貢獻
1975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有關部門在廣州召開了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座談會。會上制定了《1975—1985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準備在十年內出版160部中外語文詞典。《漢語大詞典》就在其中。
《漢語大詞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漢語語文詞典。羅竹風先生任第一版主編,王力、葉圣陶、朱德熙、張世祿、張政烺等著名學者任顧問,華東地區五省一市(魯、蘇、皖、浙、閩、滬)400多位學者參加編纂。此書于1986年出版第一卷,1994年出齊正文十二卷、附錄及索引一卷。全書收條目37萬,總字數5000余萬,插圖2253幅。通過長期認真研讀,王锳對《漢語大詞典》作出了這樣的判斷:“《漢語大詞典》與《漢語大字典》是我國辭書編纂史上的雙璧,反映了我國辭書編纂的最新最高成就。但人無完人,書無完書,由于種種原因,《漢語大詞典》也存在諸多不足。”憑借扎實的學術基礎,王锳對此書提出了很多增補、修訂意見,先后出版了《〈漢語大詞典〉商補》《〈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兩部專著。
《〈漢語大詞典〉商補》共收入600余條商補意見,涉及六個方面的問題:立目商補、釋義商榷、義項商補、闕例增補、提前書證、引文斠議。如“臂膀”一詞,《漢語大詞典》釋為“胳膊”,僅此一義。《〈漢語大詞典〉商補》指出,“臂膀”條當補“比喻助手”的常用義,《說岳全傳》第四十七回:“本帥親自出馬去,收降這個英雄做個臂膀。”再如“到了”一詞,《漢語大詞典》釋為“到底;畢竟”,首引唐吳融詩《武關》:“貪生莫作千年計,到了都成一夢間。”《〈漢語大詞典〉商補》指出,《全唐詩》錄此詩“間”作“閒”,為“閑”字別體,修訂本《辭源》“到了”目亦引作“間”,均誤。
《〈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也把商討的條目分為六類:辨釋義、考語源、補詞目、增義項、添例證、校引文。如“頒獎”一詞,《漢語大詞典》:“對在某項競賽中的個人或集體頒發獎金、獎品或獎狀等,給予鼓勵。”例句引自1991年3月27日《文匯報》。《〈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指出,此詞并非純粹的現代語詞,至遲宋代已見。《冊府元龜》卷一二八:“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敕,征討徐州將士等委吏部度支頒獎有差。”王锳還對釋文提出了修改意見:“另,釋文過于現代化,‘對在……或集體’十五字可刪。”再如“戴高帽子”一詞,《漢語大詞典》引《鏡花緣》第二七回:“老父聞說此處最喜奉承,北邊俗語叫作愛戴高帽子。”《〈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指出:“引文之前原有‘多九公道’四字,‘老父’當為‘老夫’之誤,‘老夫’系多九公自稱。”
王锳不僅對許多條目的編寫提出了具體意見,而且對全書的編纂原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關于《漢語大詞典》的修訂,有一種意見認為,《漢語大詞典》應該容納古今漢語的一切方面,越大越全越好。王锳認為這樣的意見值得商榷,“它違背了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趨勢和原則,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也一樣,單就漢語辭書這一塊說,實現上述目標應該是漢語辭書系列,而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哪一部辭書。《漢語大詞典》修訂,從縱向看應當同《現代漢語大詞典》分工,從橫向看則應和修訂本《辭源》《辭海》以及不止一種古今方言大詞典分工”,“辭書修訂通常比較注意的是增補的一面,而應該刪減的一面往往被忽略”。王锳強調,《漢語大詞典》修訂,不必計較冊數的多少,而是既要補其所當補,又要注意減肥瘦身。為此,他提出了“動小手術”與“動大手術”兩種路徑,通過小手術、大手術結合,給《漢語大詞典》“瘦身”。
王锳所說的“動小手術”,包括三種辦法:1.刪除釋文中的冗余信息。比如“池鹽”條釋義:“從咸水湖采取的鹽,成分和海鹽相同。我國西北各地和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等地出產很多。古時量地為畦,引含鹽分的沃之,稱作種鹽,水耗則鹽成,即為池鹽。”他認為,《漢語大詞典》作為語文詞典,只需保留前一句或兩句即可,其后均宜刪去。2.刪除錯誤義項。比如“骯臟”條的“比喻卑鄙、丑惡”義,《漢語大詞典》引明周茂蘭《王五癡積制錢為佛像五軀送供虎丘禪院》詩:“豈其骯臟存胸次,恭成法相系所思。”王锳認為,“骯臟”有“比喻卑鄙、丑惡”義,僅據這一孤證得出,而且《王五癡積制錢為佛像五軀送供虎丘禪院》是贈人之作,作者不應在詩中痛斥對方卑鄙、丑惡。單就詩題及所引的這一聯的對句“恭成”“系所思”的措辭看,作者是在褒揚對方而非貶斥對方,再通讀全詩,更可知編者所概括的義項是有問題的。3.刪除某些詞目。這些應該刪除的詞目又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割裂文義的假詞,如“須管教”條實際上是把“須管”和“教”兩詞誤合為一;其二是生僻的文壇掌故,這應讓位給修訂本《辭源》;其三是流行區域小、偶見的方言詞,最好不收,可以交給專門的方言詞典來收錄。
王锳所說的“動大手術”,涉及詞典本身的性質。他指出,《漢語大詞典》作為大型歷時性的漢語辭書,原來的編輯方針“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無可厚非,但是,為了減肥瘦身,統籌兼顧,這一方針可以改“今”為“近”。他建議,《漢語大詞典》收詞時限到清代中葉為止,此后的任務一概交給《現代漢語詞典》以及《現代漢語大詞典》。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使詞典本身的性質更明確,定位更恰當。作為漢語歷史詞典,《漢語大詞典》只負責解決清中葉以前漢語詞匯查考和研究的需要。第二,可以使參加修訂的編纂人員集中精力,抓好中古和近代漢語這一大段漢語詞匯短板的補充增訂,把近年來中古和近代漢語詞匯研究的成果真正吸收進來。第三,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部分,這主要體現在現當代。現當代漢語不僅變化速度快,而且問題復雜。只管歷史,不管現當代,可以增強詞典的相對穩定性。
王锳的這些觀點,既為《漢語大詞典》修訂提供了參考,也值得其他語言工具書的編寫者借鑒。
名垂后世
大約是1994年至1995年間,我和老伴王立俠女士去貴陽,參加中國旅游報刊協會評選優秀旅游報刊的活動,幾次與王锳相見暢談。貴陽市區有山,其中一座好像叫黔靈山,在山腳有茶室。我們夫妻和王锳曾在茶室小聚,品茗談心,十分愜意。
2005年,王锳左肺發現癌細胞,住院做了一次手術。身體康復后,他又在不知疲倦地從事學術研究。一轉眼到了2015年,這一年我遇到大不幸,我的老伴患肝癌去世,老伴去世的悲傷一直在折磨著我。這一年的7月8日,我接到王锳從貴陽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癌細胞已經轉移到右肺,需要住院治療。我安慰他,要他積極與大夫配合,爭取早日康復。過了十天,也就是7月18日,我又接到他的電話,他告訴我這次很麻煩,癌癥在擴散,還要開刀。我除了安慰他,還有別的辦法嗎?我心中默默祈禱,希望出現奇跡。
可是奇跡沒有發生,在苦盼了幾天后,我收到他不幸去世的信息,許多往事都浮上心頭。曾在貴陽山腳茶室小聚的三個人,因癌癥走了兩人,只剩我一人。王锳調入貴州大學前的職稱是講師,在貴大直接晉升為教授。審閱他的論文并提出直接晉升意見的是呂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北大中文系1957級語言班有28人,最后成為語言學家的只有四人,就是貴州大學的王锳、復旦大學的孫錫信、北京大學的蔣紹愚和我。時至今日,王锳和孫錫信都去世了,只剩下紹愚和我。
王锳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他熱愛語言學事業,幾十年埋頭苦干,頑強拼搏,為中國語言學開創了一片新天地。王锳雖然走了快十年,但是他精心撰著的文章仍在社會流傳,閃閃發光,造福社會。
本版圖片由王锳之女王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