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þ£∫Ö«≥±∫£ ÜŒŒª£∫¡xûı –Œƒ ∑—–æ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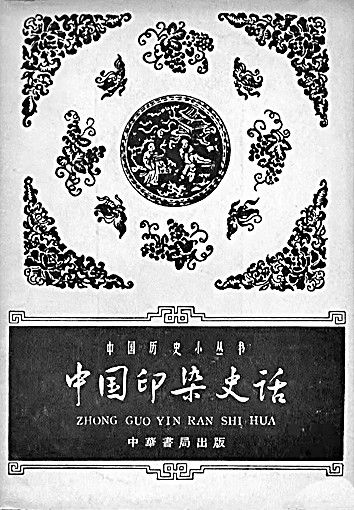


¸SƒÐ•¿L°∂Â\ÎuÇH∞È°∑ ŸY¡œàD∆¨
°æ«ÛÀ˜°ø
åW(xu®¶)»À–°Ç˜
¸SƒÐ•£®1924°™2016£©£¨’„Ω≠¡xûı»À°£∑˛Ôó ∑°¢ΩzæI ∑壺“°£1950ƒÍøº»Î∫º÷ðᯡ¢Àá壣®∫Û∏¸√˚ûÈ°∞÷–—Î√¿–g(sh®¥)åW(xu®¶)‘∫»Añ|∑÷‘∫°±£©£¨1953ƒÍÆÖòI(y®®)”⁄÷–—Î√¿–g(sh®¥)åW(xu®¶)‘∫π§Àá√¿–g(sh®¥)œµ£¨¡Ù–£◊x—–æø…˙£¨1955ƒÍ—–æø…˙ÆÖòI(y®®)£¨¡Ù–£»Œ÷˙Ωð£1956ƒÍ’{(di®§o)»Î÷–—Îπ§Àá√¿–g(sh®¥)åW(xu®¶)‘∫£®Ωҫ»A¥ÛåW(xu®¶)√¿–g(sh®¥)åW(xu®¶)‘∫£©°£÷¯”–°∂÷–á¯ΩzæIø∆ººÀá–g(sh®¥)∆þ«ßƒÍ°∑°∂÷–á¯∑˛—b ∑°∑°∂÷–á¯öv¥˙—bÔóºyò”¥Ûµ‰°∑µ»£¨÷˜æé°∂÷–á¯√¿–g(sh®¥)»´ºØ°§π§Àá√¿–g(sh®¥)æé°§”°»æøó¿C°∑µ»°£
15ƒÍ«∞µƒ“ªÃÏ£¨Œ“µΩ±±æ©∞ð‘L¡xûı¿œýl(xi®°ng)¸SƒÐ•œ»…˙°£“ª◊þþM(j®¨n)À˚º“£¨÷ª“äøÕèd◊Ó–—ƒøµƒŒª÷√íÏ÷¯“ª∑˘˝à≈€øóÂ\£¨∞µΩ…´µƒµ◊◊”£¨…œ√Ê¿Cµƒ˝àËÚËÚ»Á…˙°£∑˛Ôó ∑≈cΩzæI ∑’˝ «¸SƒÐ•“ªðÖ◊”◊Œ◊Œ“‘«Ûµƒ ¬òI(y®®)°£
é◊Èg¬™ “åë–¬àD
¸SƒÐ•1924ƒÍ≥ˆ…˙”⁄¡xûı≥Ì≥«£¨‘≠√˚¸SƒÐ∏£°£¸Sº“‘≠ «ÇÄπŸª¬»Àº“£¨‘¯Ô@∫’“ªïr£¨ø…”…”⁄¸SƒÐ•µƒÝîÝî°¢∂˛≤Æ≤ƻ慜¡À≥È¥Ûüüµƒê∫¡ï(x®™)£¨∞—º“¿ÔµƒÂXª®π‚¡À£¨÷ªµ√◊ÉŸuº“Æa(ch®£n)°¢ÞD(zhu®£n)◊åÕ¡µÿ£¨”⁄ «º“µ¿÷–¬‰°£
1942ƒÍ£¨¸SƒÐ•èƒ¡xûıøh¡¢÷–åW(xu®¶)“ÞòI(y®®)£¨«∞Õ˘Ã√–÷ì˙(d®°n)»Œ–£ÈLµƒ”¿øµ–¬»∫∏þ÷–åW(xu®¶)¡ï(x®™)¡À∞΃Íúy¡ø£¨¥À∫ÛþM(j®¨n)»Î’„Ω≠ °úy¡øÍÝ£¨≥…ûÈå£òI(y®®)úy¿LÜT°£“∞Õ‚π§◊˜Îm–¡øý£¨µ´úy¿Lºº–g(sh®¥)ûÈÀ˚∫ÛÅ̵ƒ∑˛Ô󌃪ؗ–æøπ§◊˜¥Úœ¬¡À“ª∂®ª˘µA(ch®≥)°£1949ƒÍ£¨À˚±ªƒ∏–£¡xûı÷–åW(xu®¶)∆∏ûÈ’ZŒƒΩÃÜTºÊ ¬Ñ’(w®¥)ÜT°£
¸SƒÐ•èƒ–°ê€ÆãÆ㣨≥£‘⁄ⶅœÆãʃѰ»ÀŒÔ°£1950ƒÍ£¨À˚“‘Õ¨µ»åW(xu®¶)¡¶øº»°∫º÷ðᯡ¢Àá壣®Æî(d®°ng)ƒÍ11‘¬∏¸√˚ûÈ°∞÷–—Î√¿–g(sh®¥)åW(xu®¶)‘∫»Añ|∑÷‘∫°±£©£ª“Ú‘∫œµ’{(di®§o)’˚£¨1953ƒÍƒÍ≥ı£¨ÞD(zhu®£n)»Î±±æ©µƒ÷–—Î√¿–g(sh®¥)åW(xu®¶)‘∫π§Àá√¿–g(sh®¥)œµåW(xu®¶)¡ï(x®™)£¨±æø∆ÆÖòI(y®®)∫Û¡Ù–£¿^¿m(x®¥)◊x—–æø…˙°£¸SƒÐ•èƒþ@ïrÈ_ º◊∑ÎS…Ú背ƒœ»…˙—–æø÷–á¯∑˛Ôó ∑°£—–æø…˙ÆÖòI(y®®)∫Û£¨¸SƒÐ•¡Ù–£»ŒΩð£1956ƒÍ£¨÷–—Îπ§Àá√¿–g(sh®¥)åW(xu®¶)‘∫≥…¡¢£¨À˚’{(di®§o)»Î‘ì–£»æøóœµπ§◊˜°£
üo’ì «◊ˆåW(xu®¶)…˙£¨þÄ «ΩÃï¯÷ŒåW(xu®¶)£¨¸SƒÐ•∂º «ÇÄ∆¥√¸»˝¿…°£èƒ20 ¿ºo(j®¨)80ƒÍ¥˙≥ı÷±÷¡2012ƒÍ£¨À˚é◊∫ı√øƒÍ≥ˆ∞Ê“ª±æ∑˛Ô󌃪ØÓI(l®´ng)”Úµƒ÷¯◊˜°£èƒƒÍΩ¸ª®º◊È_ º£¨≥÷¿m(x®¥)Ω¸30ƒÍ£¨ƒÍæ˘≥ˆ“ª±æ∏þŸ|(zh®¨)¡ø°¢∏þÀÆ∆Ωµƒ∑˛Ô󌃪ؗ–æø∑Ω√ʵƒï¯£¨À˚µƒ∆D–¡≈¨¡¶ø…œÎ∂¯÷™°£
°∞÷–ᯔ–∂YÉx÷Æ¥Û£¨π ∑Qœƒ£ª”–∑˛’¬÷Æ√¿£¨÷^÷Æ»A°£°±£®°∂¥∫«Ô◊Ûǘ’˝¡x°∑£©‘Á‘⁄¥∫«Ô÷–ÕÌ∆⁄£¨Œ“᯵ƒøó‘ϺºÀáæÕ“—Ωõ(j®©ng)∑«≥£æ´’ø£¨øºπ≈∞l(f®°)¨F(xi®§n)µƒ“ªâKé◊∫ŒºyøóÂ\Ωõ(j®©ng)æĵƒ√Ð∂»∏þþ_(d®¢)√ø¿Â√◊240∏˘°£¸SƒÐ•◊´å뵃°∂÷–á¯öv¥˙—bÔóºyò”¥Ûµ‰°∑£¨¿Ô√Ê ’»Î¡À6000∂ý∑˘ºyò”£¨∂º «À˚é◊ ƃÍÅÌ“ªπP“ªπPÆã≥ˆÅ̵ƒ°£À˚ªÿÓô°∂÷–á¯ΩzæIø∆ººÀá–g(sh®¥)∆þ«ßƒÍ°∑µƒæé◊Îöv≥ã∫°∞±»∑Ω“ªâK≤º£¨À¸ «”…Ωõ(j®©ng)æÄ°¢æïæÄΩMøó≥…ª®ºyµƒ£¨À¸µƒΩMøó≤ª÷π“ªå”£¨ «∫√é◊唵ƒ£¨þ@ÇÄΩMøó «‘ı√¥ò”µƒ£ø «‘ı√¥øó≥ˆÅ̵ƒ£øΩY(ji®¶)òã(g®∞u) «‘ı√¥ò”µƒ£ø”√¡¢ÛwÔ@Œ¢ÁR∑≈µΩ25±∂¥Û–°µƒïr∫Ú◊Ó«Â≥˛£¨‘Ÿ¥Û¡ÀæÕø¥≤ª«Â£¨–°¡À“≤ø¥≤ª«Â£¨25±∂◊Û”“£¨”√¡¢ÛwÔ@Œ¢ÁR∞—ΩMøóÜŒŒª’“≥ˆÅÌ£¨À¸µƒΩY(ji®¶)òã(g®∞u) «‘ı√¥ò”µƒ£¨ΩoÀ¸Æã≥ˆÅÌ°£þ^»•»À∂º «‘⁄–°∏Ò◊”…œ”√¸c◊”¸c£¨»Àº“ø¥≤ª«Â≥˛°£Œ“ «ΩoÀ¸”√Ω‚∆ ∏˙Õ∏“ïΩY(ji®¶)∫œ∆ÅÌÆ㣨“ÚûÈŒ“ «åW(xu®¶)√¿–g(sh®¥)µƒ£¨“ªå”“ªå”þ@ò”Æã≥ˆÅÌ£¨Œ“ΩoÀ¸∂ºÆã«Â≥˛¡À°£°±£®°∂Â\¿C¡˜π‚°™°™¸SƒÐ•ø⁄ ˆ ∑°∑£©
þ@“ªπP“ªπPµƒÆ㣨 «‘⁄òO∆‰∆Døýólº˛œ¬ÕÍ≥…µƒ°£À˚µƒ∑Ú»ÀÍêæÍæÍ£¨É∫ïræÕªº…œ¡ÀÔL(f®•ng)ùÒ–‘–ƒ≈K≤°£¨°∞…ÌÛw≤ª∫√£¨¿œ◊°‘∫£¨–ƒ≈K≤ª∫√£¨¿œ «–ƒº°π£À¿£¨¿œìåæ»°£∫ÛÅÌ◊°·t(y®©)‘∫£¨”÷ìQ¡À–ƒ≈Kµƒ∞̓§£¨ΩoÀ˝∞≤—b∆≤´∆˜£¨∂ºõ]πД√°≠°≠∫ÛÅÌ”÷µ√¡À∞©∞Y£¨»ÈœŸ∞©°≠°≠°±Æî(d®°ng)ïrŸIÀé∫пßÎy£¨°∞·t(y®©)‘∫¿ÔÈ_¡ÀÀ飨µΩ“ªº“ÀéµÍ≈‰≤ª»´£¨’“µΩƒƒº“”–þ@ÇÄÀ飨÷ªƒÐ≈‰“ª∑˛£¨µ⁄∂˛∑˛æÕµ√µ⁄∂˛ÃÏ“ª‘ÁÚTÐáµΩƒ«ÀéµÍÈTø⁄»•≈≈ÍÝŸI°£À˘“‘£¨ƒ«ïr∫Ú±±æ©þ@–©ÀéµÍƒƒ“ªº“ÀéµÍ ≤√¥ïr∫ÚÈ_ÈT£¨Œ“∂º÷™µ¿°≠°≠√øÃÏ“ª‘Á∆ÅÌæÕÞD(zhu®£n)“ª¥Û»¶£¨»ª∫Ûœ¬¡À∞ý£¨þĵ√ŸIÀ飨’˚Çı±æ©≥«Œ“√øÃÏÚTÐáÞD(zhu®£n)“ª±È°£°±£®Õ¨…œï¯£©”–ïr∫Ú£¨À˚¡Ë≥ø“ª¸cÁäæÕ“™»•·t(y®©)‘∫≈≈ÍÝíÏÃñ°£∞§µΩ‘Á…œ£¨íÏ…œ¡ÀÃñ£¨¸SƒÐ•”÷µ√ÚTÐáªÿº“Ω”∑Ú»ÀµΩ·t(y®©)‘∫£¨ø¥ÕÍ≤°£¨∞—À˝ÀÕªÿº“£¨‘Ÿ⁄sµΩåW(xu®¶)–£…œ∞ý£¨√øÃÏ∂º Æ∑÷∆£ëv°£
ƒ«ïr£¨¸SƒÐ•∞◊ÃÏ…œ∞ý°¢Ωo∑Ú»Àø¥≤°°¢ŸIÀ飨þÄ“™◊ˆº“Ñ’(w®¥)£¨õ]ïrÈgåë◊˜°£÷ª”–µ»µΩÕÌ…œ£¨∑Ú»À°¢∫¢◊”ÀØ÷¯¡À“‘∫Û£¨≤≈“ªÇÄ»À«ƒ«ƒµΩÍñ≈_…œåëñ|Œ˜°£ƒ« «“ªÇÄõ]”–∑‚È]µƒÍñ≈_£¨œƒÃÏø· Ó£¨¸SƒÐ•÷ª¥©“ªól—ùÒ√“≤≤ª”Xµ√õˆøÏ£¨∂¨ÃÏ¥©÷¯√Þ“¬þÄ¿‰µ√≤ªµ√¡À°£æÕ «þ@ò”£¨À˚√øÃÏ∂ºåëµΩ∞Î“π£¨”√¡À“ªƒÍ∂ýïrÈg£¨ΩK”⁄åëÕÍ¡À°∂÷–á¯∑˛—b ∑°∑°£∫ÛÅÌ»•Ûwôzµƒïr∫Ú£¨À˚≤≈÷™µ¿£¨—™â∫“ªœ¬◊”∏þ¡À≤ª…Ÿ°£
Æî(d®°ng)ïr¸SƒÐ• ’»ÎµÕ£¨õ]”–∂ý”ýµƒÂXŸIﯣ¨ŸIœýôC(j®©)»•≈ƒŒƒŒÔ∏¸≤ª¨F(xi®§n)å磨ûÈ¡À°∞“‘ŒÔ◊C ∑°±£¨À˚÷ªƒÐ≤ªÞo–¡øýµÿÆ㌃ŒÔ°£√ø¥Œ≥ˆ≤Ó»•Õ‚µÿ≤©ŒÔ^£¨’“µΩ≈cÀ˚—–æø”–ÍP(gu®°n)œµµƒŒƒŒÔ£¨À˚øÇ «œ»”√„UπPÆã≥ˆ≤ð∏£¨»ª∫ÛªÿµΩ◊°Ã飨∞·ÅÌ–°µ ◊”£¨≈ø‘⁄¥≤…œ¿^¿m(x®¥)”√√´πPÕÍ…∆°£
”–“ª¥Œ»•∏£Ω®øº≤ÏÀŒ¥˙¸SïNƒπ£¨ŸY¡œ∂—∑≈‘⁄∑‚È]µƒÇ}éÏ¿Ô£¨≠h(hu®¢n)æ≥∑«≥£≥±ùÒ£¨∫ÕÀ˚Õ¨»•µƒé◊Œªå£º“Îy“‘»Ã У¨∫ÜÜŒ¡ÀΩ‚“ªœ¬æÕ¥“¥“ÎxÈ_¡À£¨∂¯¸SƒÐ•Ös√øÃÏÕ˘Ç}éÏ¿Ô„@£¨’∆Œ’¡À¥Û¡øµ⁄“ª ÷≤ƒ¡œ£¨ûÈ°∞“‘ŒÔ◊C ∑°±Ã·π©¡ÀœËåç’ìì˛(j®¥)°£
ÔL(f®•ng)—©…ÚÈTÕ–∏∂≥ı
¸SƒÐ•µƒåW(xu®¶)–g(sh®¥)µ¿¬∑µ√µΩ¡À…Ú背ƒ°¢èàÿÍ°¢˝ãÞπ¨l°¢≤ÒÏÈ°¢èàπ‚”Ó°¢¿◊πÁ‘™µ»åW(xu®¶)’þµƒéÕ÷˙°£”»∆‰ «…Ú背ƒœ»…˙£¨å¶À˚”∞Ìë∫Ð¥Û°£
¸SƒÐ•‘⁄÷–—Î√¿–g(sh®¥)åW(xu®¶)‘∫◊x—–æø…˙µƒïr∫Ú£¨≈cÀ˚Õ¨∞ýµƒé◊Œª¡ÙåW(xu®¶)…˙œÎåW(xu®¶)¡ï(x®™)÷–á¯ΩzæI ∑£¨ø… «åW(xu®¶)–£õ]”–þ@∑Ω√ʵƒ¿œéü£¨æÕ∆∏’à…Ú背ƒœ»…˙ÅÌ»ŒΩð£…Ú背ƒœ»…˙÷v‘í”–œÊŒ˜ø⁄“Ù£¨¡ÙåW(xu®¶)…˙¬Ý≤ª∂Æ£¨åW(xu®¶)–£æÕ◊å¸SƒÐ•≈cÀ˚ÇÉ“ª∆¬Ý’n£¨’n∫Û∞—À˚µƒ’nÃ√πP”õ’˚¿Ì≥ˆÅÌΩo¡ÙåW(xu®¶)…˙Ö¢øº°£”⁄ «£¨¸SƒÐ•”–¡À∫Õ…Ú背ƒœ»…˙≥Øœ¶œýÃ鵃ôC(j®©)ï˛°£
Æî(d®°ng)ïr£¨±±æ©«∞ÈTÕ‚”–∫Ð∂ýπ≈∂≠µÍ£¨ €Ÿu“ª–©π≈¥˙∑˛—b°¢¥Ã¿C∆∑°£…Ú背ƒœ»…˙≥£éßåW(xu®¶)…˙»•åçµÿ”^ø¥þ@–©π≈∂≠°£ì˛(j®¥)…Ú背ƒ1978ƒÍ5‘¬Ωo∫˙ÜÃ浃–≈÷–÷v£¨ÉH‘⁄1952ƒÍ£¨À˚æÕ”√¡Àºs40ÃÏ£¨°∞“ªπ≤¥Ûºsø¥¡À∞Àæ≈ ƺ“¥Û–°ŒƒŒÔ…õͣ¨Ωõ(j®©ng) ÷þ^—€¡À¥Ûé◊ Æ»f∏˜∑N∏˜ò”ŒƒŒÔ°±°£√øÆî(d®°ng)…Úœ»…˙»•π≈∂≠µÍµƒïr∫Ú£¨≥£”–É…ÇăÍðp»À≈„∞È◊Û”“£¨“ªÇÄ «¸SƒÐ•£¨¡Ì“ªÇÄ «ÍêæÍæÍ°£
…Ú背ƒƒ«ïr‘⁄÷–á¯öv ∑≤©ŒÔ^π§◊˜£¨µ´Ωõ(j®©ng)≥£µΩπ åm◊ˆ—–æø°£…Úœ»…˙“™—–æø÷–á¯∑˛—b ∑£¨Ã”≤ªþ^ΩzæIöv ∑£¨∂¯π åm ’≤ÿ¡Àå¢Ω¸20»fº˛Ωz¿C∆∑°£“ª–©å£º“£¨∞¸¿®…Úœ»…˙£¨µΩπ åm≤È’“œýÍP(gu®°n)Ωz¿C∆∑£¨“ÚûÈ≤ÿ∆∑ô∂ý£¨∆‰À˚π§◊˜»ÀÜT“ªœ¬◊”’“≤ªµΩ£¨÷ª”–“ªŒªΩ–ÍêæÍæ͵ƒ–°π√ƒÔ÷µ∞ýïr£¨å£º“ÇÉ°∞¡¢µ»ø…»°°±°£…Ú背ƒœ»…˙ÃÿÑeœ≤ögÍêæÍæÍ£¨¿œ’àÀ˝éÕ√¶£¨þÄΩõ(j®©ng)≥£∞—À˝’àµΩº“¿Ô°£
°∞…Úœ»…˙∏˙éüƒ∏£®èà’◊∫Õ£©∂Y∞ð¡˘»•≥‘Œ˜≤Õ£¨æÕ¥ÚÎä‘íΩ–ÍêæÍæÍ“ª∆»•£¨æÕ∏˙◊‘º∫≈ÆÉ∫“ªò”ø¥¥˝°£“ª÷±∂ý…ŸƒÍ£¨Œ““≤Ωõ(j®©ng)≥£µΩ…Úœ»…˙º“¿Ô»•£¨∫ÕÍêæÍæÍ∂º «‘⁄“ª∆°£°±“ªÅÌ∂˛»•£¨¸SƒÐ•°¢ÍêæÍæÍ Ïœ§∆ÅÌ£¨ΩY(ji®¶)ûÈÿ¯É´£¨…Úœ»…˙üo–Œ÷Æ÷–≥…¡ÀÀ˚Çɵƒ°∞‘¬œ¬¿œ»À°±°£
…Ú背ƒœ»…˙嶸SƒÐ•°¢ÍêæÍæÍþ@É…ŒªƒÍðp÷˙ ÷∫Ð «Ÿp◊R£¨Ωõ(j®©ng)≥£ƒÕ–ƒµÿ÷∏åß(d®£o)À˚Çɵƒ—–æøπ§◊˜°£‘⁄Õ̃Í≤°Õ¥¿p…Ìïr£¨…Ú背ƒ∞—‘S∂ý’‰ŸFµƒ ÷∏ŸY¡œÀÕΩoþ@å¶∑Ú∆Þ£¨≤¢æþÛw÷∏åß(d®£o)»Á∫Œ”…±Ìº∞¿ÔµÿþM(j®¨n)––—–æø£¨œ£Õ˚À˚ÇÉ‘⁄∑˛Ô󌃪ØÓI(l®´ng)”ڃЅӻΜ¬»•°£
1958ƒÍ£¨÷¯√˚öv ∑åW(xu®¶)º“֫͜÷◊hæ铪Ã◊Õ®À◊µƒöv ∑◊xŒÔ°™°™°∞÷–á¯öv ∑–°Ö≤ﯰ±£¨÷–—Îπ§Àá√¿–g(sh®¥)åW(xu®¶)‘∫≤º÷√¸SƒÐ•◊´åë°∂÷–ᯔ°»æ ∑‘í°∑°£æÕ’˝ Ω≥ˆ∞ÊŒÔ∂¯—‘£¨þ@ «À˚µƒÃé≈Æ◊˜£¨åëµ√∏ÒÕ‚’J(r®®n)’Ê°£≥ı∏–Œ≥…∫Û£¨¸SƒÐ•’à…Ú背ƒœ»…˙÷“‚“ä°£…Úœ»…˙ø¥µΩï¯∏Â÷–”√¡À°∞ì˛(j®¥)’f°±þ@ò”µƒ±Ì ˆ£¨æÕ”√ºtπP‘⁄∏Â◊”…œÆã¡ÀÇÄ¥ÛÜñÃñ£¨≤¢≈˙◊¢°∞ì˛(j®¥)’l’f°±°£…Úœ»…˙µƒ≈˙◊¢£¨¸SƒÐ•øÃπ«„ë–ƒ£¨°∞ƒ« «◊匓“ªðÖ◊””õ◊°µƒΩÔ˝£¨À˘“‘∫ÛÅÌ≤ª∏“ÎS±„’f°±°£…Úœ»…˙µƒ’Å’ÅΩÃ’d”∞Ìë¡À¸SƒÐ•“ªðÖ◊”°£¸SƒÐ•Õ̃Íå댃’¬◊∑ëõ…Úœ»…˙£¨∏–»À÷¡…Ó°£
°∞Œƒ∏Ô°±∆⁄Èg£¨…Ú背ƒèƒ∏…–£ªÿæ©∫Û£¨◊‘º∫‘⁄ñ|Ã√◊”∫˙Õ¨◊°“ªÈg10∆Ω∑Ω√◊◊Û”“µƒ–°∑ø£¨ê€»À‘⁄–°—Ú“ÀŸe∫˙Õ¨µƒÜŒŒªÀÞ…·◊°°£™ö◊‘…˙ªÓµƒ…Ú背ƒ£¨π§◊˜∆ÅÌ≥£≥£Õ¸”õ≥‘Ôà°£”–“ªÃÏ£¨¸SƒÐ•∑ÚãD»•ø¥…Ú背ƒ£¨µΩÀ˚º““— «œ¬ŒÁ3¸c∂ý¡À£¨¿œœ»…˙æ”»ªþÄõ]≥‘ŒÁÔࣨ°∞“䌓ÇÉ?n®®i)•¡À£¨≤≈ƒ√é◊ÇÄÀÿ∞¸◊”∑≈µΩÈTÕ‚µƒ∑‰∏C√∫Ýt…œø擪ø棨≈𓪱≠≤ËæÕÀ„ «ŒÁ≤Õ¡À°±°£…Úœ»…˙…ÌÛw“≤≤ª∫√£¨”–∏þ—™â∫£¨Ωõ(j®©ng)≥£—€µ◊≥ˆ—™°£ø¥µΩþ@√¥“ªŒªŒƒ ∑æÞΩ≥£¨Ãéæ≥»Á¥À¿ßÎy£¨¸SƒÐ•√»…˙¡ÀÕÀ“‚°£
ÍêæÍæÍ∞—’…∑ÚµƒœÎ∑®∏Ê‘V¡À…Ú背ƒ£¨…Úœ»…˙º±¡À£∫°∞ƒ„ÒR…œΩ–¸SƒÐ•µΩþ@¿ÔÅ̓䌓£°°±¸SƒÐ•⁄sµΩ…Úœ»…˙º“£¨ðpðpÕ∆È_–°ŒðµƒÈT£¨“äÀ˚√Ê≥Ø¿ÔÃ…‘⁄¥≤…œ°£¬ÝµΩÈTÌ루…Úœ»…˙¬˝¬˝ÞD(zhu®£n)þ^…ÌÅÌ£¨‘Sæ√£¨ΩK”⁄Üñ¡À“ªæ‰‘í£¨°∞¬Ý’fƒ„ª“–ƒ≤ªœÎ∏…£¨“™∏ƒ––¡À£ø°±¸SƒÐ•≤ª∏“ªÿ¥£¨µ´÷™µ¿◊‘º∫œÎ∑®Âe¡À£¨°∞Œ“¬˝¬˝∑ˆ…Úœ»…˙◊¯∆ÅÌ£¨≈ıþ^»•“ª±≠ü·≤Ë£¨…Úœ»…˙∫»¡ÀÉ…ø⁄£¨Ω”÷¯’f£∫°Æƒøπ‚“™þh(yu®£n)¥Û“ª¸c£¨á¯º“≤ªƒÐõ]”–ŒƒªØ£¨≤ªƒÐõ]”–ǘΩy(t®Øng)°£°Ø¥ÀïrÀ˚±Ì«Èá¿(y®¢n)√C£¨‘í“ÙµÕ≥¡°£þ@»˝æ‰‘픿þh(yu®£n)‘⁄Œ“–ƒµ◊£¨º§ÑÓŒ“÷ªƒÐ«∞þM(j®¨n)£¨≤ªƒÐ∫ÛÕÀ°£°±£®¸SƒÐ•°∂ë—ƒÓ∂˜éü…Ú背ƒ°∑£©
…Ú背ƒœ»…˙æéå뵃°∂÷–á¯π≈¥˙∑˛Ôó—–æø°∑£¨‘⁄°∞Œƒ∏Ô°±«∞æÕ“—ÕÍ≥…£¨µ´°∞Œƒ∏Ô°±È_ º∫Û£¨ï¯∏‘‚µΩ∆∆⃣¨≤ªµ√≤ªèƒÓ^◊ˆ∆£¨÷±µΩ1971ƒÍ≤≈’˝ Ω≥ˆ∞Ê°£…Úœ»…˙åëï¯ïr£¨≥ˆÕ¡µƒºèøó∆∑þÄ≤ª∂ý£¨ï¯÷–ƒÐ¿˚”√åçŒÔ≤ƒ¡œ∫Ð…Ÿ°£
°∞…Úœ»…˙“≤’J(r®®n)ûÈπ‚øøŒƒ◊÷’f≤ª«Â≥˛£¨∑˛—bøøŒƒ◊÷‘ı√¥’f«Â≥˛£øÓÅ…´ƒ„’f «ºtµƒ£¨µ´ºtµƒ”÷”–∏˜∑N∏˜ò”µƒºt£¨æG”÷”–∏˜∑N∏˜ò”µƒæG£¨ª®ºyþ@–©∂º÷v≤ª«Â≥˛£¨±ÿÌöø¥åçŒÔ°¢ø¥àD∆¨°£‘≠ÅÌ…Úœ»…˙å냫±æﯵƒŸY¡œ∫Ð…Ÿ£¨œÎ‘Ÿå듪±æ£¨µ´ «∫ÛÅÌæÕ≤°¡À£¨õ]åë≥…°£Œ“œÎ£¨“ÚûÈ…Úœ»…˙”–þ@ÇÄþz‘∏£¨¡ÌÕ‚£¨»Áπ˚å¢ÅÌÞk≤©ŒÔ^“≤–Ë“™þ@ÇÄ£¨þ@ò”Œ“æÕœ¬õQ–ƒ∏˙Œ“ꀻÀ“ª∆åëﯰ£°±”…¥Àø…“䣨ûÈ¡Àåç¨F(xi®§n)…Ú背ƒœ»…˙…˙«∞þz‘∏£¨¸SƒÐ•∑ÚãD≤≈œ¬∂®õQ–ƒ£¨æéåë°∂÷–á¯∑˛—b ∑°∑°£
20 ¿ºo(j®¨)70ƒÍ¥˙“‘∫Û£¨ºèøóøºπ≈π§◊˜’þ‘⁄»´á¯∏˜µÿ∞l(f®°)æÚ±£◊o(h®¥)¡À∂ýÃéøºπ≈þz÷∑÷–µƒºèøó∆∑ŒƒŒÔ£¨∆‰÷–æÕ”–‘⁄Ω≠Œ˜æ∏∞≤¥Ûƒπ÷–∞l(f®°)¨F(xi®§n)µƒñ|÷Ðïr∆⁄µƒ300”ýº˛ºèøó∆∑£¨þ@墌“᯺èøóåçŒÔÊúµƒïrÈgðSœÚ«∞Õ∆þM(j®¨n)÷¡¥∫«Ô÷–ÕÌ∆⁄°£þ@ûȸSƒÐ•∑ÚãDæéåë°∂÷–á¯∑˛—b ∑°∑÷π©¡À÷ÿ“™µƒåçŒÔŸY¡œ°£
èƒΩÒ≤ªÿì(f®¥)ΩzæIá¯
‘⁄60∂ýƒÍµƒåW(xu®¶)–g(sh®¥)…˙—ƒ÷–£¨¸SƒÐ•Ö¢≈c≤¢“ä◊C¡À–¬÷–á¯∑˛Ôó ∑—–æø∞l(f®°)’πµƒöv≥ð£
1953ƒÍ£¨¸SƒÐ•¥ÛåW(xu®¶)ÑÇÆÖòI(y®®)£¨æÕÖ¢≈cªIÞk»´á¯µ⁄“ªå√√ÒÈg√¿–g(sh®¥)’π”[£¨≤¢ì˙(d®°n)»Œï˛àˆπпÌΩM∏±ΩMÈL°¢…Ÿîµ(sh®¥)√Ò◊Â^^ÈL°£þ@ «–¬÷–á¯≥…¡¢∫ÛŒ“á¯≈eÞkµƒ“é(gu®©)ƒ£◊Ó¥Û°¢“é(gu®©)∏Ò◊Ó∏þµƒπ§Àá√¿–g(sh®¥)◊˜∆∑’π”[£¨”^±äþ_(d®¢)18»f»À¥Œ°£
÷–—Îπ§Àá√¿–g(sh®¥)åW(xu®¶)‘∫≥…¡¢≤ªæ√£¨À˚æÕ∏˙ÎS≤ÒÏÈœ»…˙µΩÃÏΩÚ°¢ƒœæ©°¢ÃK÷ð°¢∫º÷ð°¢…œ∫£µ»µÿ ’ºØΩzæI£¨≤¢“ª“ª—bÒ—°¢åë’f√˜°£
1958ƒÍ£¨¸SƒÐ•Ö¢≈c¡ÀœÚá¯ëc Æ÷ЃʹI(xi®§n)∂Yµƒ±±æ©°∞ Æ¥ÛΩ®÷˛°±µƒ—bÔó‘O(sh®®)”ãπ§◊˜£¨∞¸¿®»À√Ò¥Ûï˛Ã√°¢·ûÙ~≈_ᯟe^µƒµÿÃ∫‘O(sh®®)”ã“‘º∞»À√Ò¥Ûï˛Ã√Ωzøó¥∞∫ü°¢Â\¡_Ωq…≥∞l(f®°)µƒ‘O(sh®®)”ã°£1959ƒÍ£¨‘⁄∂ÿªÕŒƒŒÔ—–æøÀ˘À˘ÈL≥£ï¯¯ôµƒ∞≤≈≈œ¬£¨¸SƒÐ•≈c≥£…≥ƒ»°¢¿ÓædË¥µΩ∂ÿªÕƒ™∏þøþ≈Rƒ°öv¥˙±⁄Æã°¢≤ ÀлÀŒÔ∑˛Ô󅜵ƒàD∞∏£¨π≤’˚¿Ì≥ˆ≤ àD328∑˘°£20 ¿ºo(j®¨)70ƒÍ¥˙£¨á¯º“ŒƒŒÔæ÷≥È’{(di®§o)÷–—Îπ§Àá√¿–g(sh®¥)åW(xu®¶)‘∫≤ø∑÷ΩÃéüÖ¢º”°∞÷–»A»À√Òπ≤∫Õá¯≥ˆÕ¡ŒƒŒÔ’π”[°±µƒŒƒŒÔ≈Rƒ°°¢èÕ(f®¥)÷∆º∞‘O(sh®®)”ãπ§◊˜£¨¸SƒÐ•Ö¢≈c≥ˆÕ¡øóŒÔµƒ∑÷Œˆ°£‘⁄≤ªµΩ“ªƒÍµƒïrÈg¿Ô£¨À˚ÇÉ“‘∫˛ƒœÈL…≥ÒRÕı∂—≥ˆÕ¡ŒƒŒÔûÈ÷ÿ¸c£¨ÕÍ≥…¡À51º˛ŒƒŒÔµƒ≈Rƒ°èÕ(f®¥)÷∆°£¥À¥Œ’π”[œ»∫Û‘⁄∫£Õ‚∂ýᯒπ≥ˆ£¨Æa(ch®£n)…˙¡ÀèV∑∫á¯ÎH”∞Ìë°£
1987ƒÍ£¨÷–á¯ΩzæI≤©ŒÔ^È_ º‘⁄∫º÷ðªIΩ®£¨¸SƒÐ•±ª∆∏»ŒûÈåW(xu®¶)–g(sh®¥)øÇÓôÜñ°£À˚ÉA◊¢»´¡¶£¨“‘ÔñùMµƒü·«ÈÖ¢≈c∆‰÷–°£ûÈ¡ÀƒººØªIΩ®Ωõ(j®©ng)ŸM£¨”–ÍP(gu®°n)∑Ω√Ê’˜ºØ¡À“ª–©ΩzæI◊˜∆∑∏∞–¬º”∆¬’π≥ˆ°£∆‰÷–”–“ªº˛«¨¬°ª µ€≥Ø∑˛˝à≈€£¨ «ÃK÷ð¥Ã¿C≤©ŒÔ^èÕ(f®¥)÷∆µƒ°£‘⁄–¬º”∆¬’π≥ˆïr£¨þ@º˛˝à≈€∫РЫý≤A£¨“ªŒª”°ƒ·»AÉS‘∏≥ˆ10»f√¿‘™ŸèŸI£¨¥˙±ÌàF(tu®¢n)ÿì(f®¥)ÿü(z®¶)»À¥ë™(y®©ng)≥ˆ €°£¬ÝµΩþ@“ªœ˚œ¢£¨¸SƒÐ•º±¡À£¨å¶ÌîÓ^…œÀæ’f£∫°∞≤ª––£°ƒ„“™Ÿu≥ˆ»•£¨Œ“∏˙ƒ„∆¥√¸£°°±‘⁄À˚µƒì˛(j®¥)¿Ì¡¶Ý霬£¨þ@º˛˝à≈€øÇÀ„õ]≥ˆ◊壨»ÁΩÒ≥…¡À÷–á¯ΩzæI≤©ŒÔ^µƒ÷ÿ“™ ’≤ÿ÷Æ“ª°£≤ªÉH»Á¥À£¨À˚þÄþB¿m(x®¥)∂ýƒÍûÈ÷–á¯ΩzæI≤©ŒÔ^éßåW(xu®¶)…˙£¨∏¸üoÉîæËŸõ¡À◊‘º∫ÈLƒÍƒ°¿L°¢‘O(sh®®)”ã°¢ ’≤ÿµƒΩzæIàD∞∏ŸY¡œ°¢ò”±æ£¨¥Û¥ÛÿS∏ª¡Àþ@ÇÄ≤©ŒÔ^µƒ’πÍêÉ»(n®®i)»ð°£
÷–á¯ΩzæI≤©ŒÔ^ªIΩ®≥…π¶∫Û£¨œýÍP(gu®°n)ÓI(l®´ng)åß(d®£o)∂ý¥ŒÕÏ¡Ù¸SƒÐ•‘⁄∫º÷ðπ§◊˜£¨¥˝”ˆÉû(y®≠u)‰◊°£ø… «Æî(d®°ng)¬ÝµΩ±±æ©’˝‘⁄ªIÞk“ªº“¥Û–Õöv ∑∑˛Ôó≤©ŒÔ^µƒœ˚œ¢£¨¸SƒÐ•”÷“„»ªõQ»ªªÿµΩ¡À±±æ©£¨¿^¿m(x®¥)◊‘º∫µƒ—–æøπ§◊˜°£
èƒ÷–á¯√¿–g(sh®¥)º“Öf(xi®¶)ï˛ ⁄”˵ƒ°∞◊ø”–≥…æÕµƒ√¿–g(sh®¥) ∑’캓°±∑QÃñµΩ᯺“àDﯙѣ¨¸SƒÐ•÷¯ ˆµ»…Ì£¨≤ªîýÕ∆Ñ”∑˛Ôó ∑°¢ΩzæI ∑µƒ—–æø£¨“≤´@µ√¡À÷T∂ýòs◊u(y®¥)£¨õ]”–πºÿì(f®¥)…Ú背ƒµƒá⁄Õ–°£°∂÷–»A∑˛ÔóÀá–g(sh®¥)‘¥¡˜°∑≥ˆ∞Ê∫Û£¨∫˙ÜÃæ‘⁄Ωo¸SƒÐ•µƒ–≈÷–å뵿£∫°∞…Ú£®èƒŒƒ£©œ»…˙æ≈»™”–÷™£¨“ýÆî(d®°ng)ûÈ◊∑ÚãD–¬◊˜≥…π¶∂¯∫¨–¶“”°£°±
”–åW(xu®¶)’þ÷∏≥ˆ£¨¸SƒÐ•‘⁄Ÿs¿m(x®¥)…Ú背ƒ°∞ ∑å窕◊C°±—–æø∑Ω∑®µƒª˘µA(ch®≥)…œ£¨∞—°∞∂˛‘™ª•◊C°±Õÿ’πµΩ°∞∂ý‘™ª•◊C°±£¨å¢»æøó‘O(sh®®)”ã≈cÕ¨ïr∆⁄µƒŒƒ´I(xi®§n)”õðd°¢∆‰À˚π§Àá√¿–g(sh®¥)∑NÓêþM(j®¨n)––œµΩy(t®Øng)–‘µƒª•◊C—–æø£¨èƒøóôC(j®©)ΩY(ji®¶)òã(g®∞u)°¢øó‘Ï‘≠¿ÌµƒΩ«∂»≥ˆ∞l(f®°)嶻æøóÀá–g(sh®¥)µƒöv ∑—ð◊É≈cÔL(f®•ng)∏Ò–Œ≥…◊∑±æÀð‘¥£¨“˝»ÎÕ∏“ïåW(xu®¶)°¢Ω‚∆ åW(xu®¶)µ»—–æø∑Ω∑®…Ó»Î∑÷ŒˆøóŒÔµƒÉ»(n®®i)≤øΩMøóΩY(ji®¶)òã(g®∞u)≈càD∞∏°¢ºy¿Ì°¢π¶ƒÐµ»÷ÆÈgµƒÍP(gu®°n)œµ£¨ø∆åW(xu®¶)Ω‚Œˆ»æøó‘O(sh®®)”ã‘≠¿Ì£¨å¢Àá–g(sh®¥)—–æøø∆åW(xu®¶)ªØ°££®¡ŒË§°¢Ö«–l(w®®i)°∂÷–᯻æøó‘O(sh®®)”ãΩÔ˝µÏª˘»À¸SƒÐ•‘O(sh®®)”ãΩÔ˝ÀºœÎÃΩŒˆ°∑£©
¸SƒÐ•°¢ÍêæÍæÍ∑ÚãD∫œ◊˜◊´å뵃°∂÷–á¯ΩzæIø∆ººÀá–g(sh®¥)∆þ«ßƒÍ°∑≥ˆ∞Ê∫Û∫√‘u»Á≥±°£÷¯√˚åW(xu®¶)’þÒT∆‰”π’f£∫°∞þ@≤øå£÷¯£¨“‘ΩzæIûÈ÷––ƒ£¨√Ë ˆ¡À÷–»A√Ò◊µƒŒƒªØ ∑£¨”√ŒƒŒÔøº◊C’π¨F(xi®§n)¡À÷–»A√Ò◊Â∆þ«ßƒÍµƒÝNÝÄŒƒªØ°£Õ¨ïr≈c±ä∂ýªÞù≠Îy∂Ƶƒøºπ≈ﯺÆ≤ªÕ¨£¨◊˜’þ π”√¡À«ÂŒ˙°¢¡˜ï≥°¢…˙Ñ”µƒ’Z—‘£¨◊å»À‘Ω◊x‘Ω”Xµ√”–“‚Àº£¨À˘“‘’fÀ¸ ««∞üoπ≈»À∫ÛüoÅÌ’þµƒ°¢Ñùïr¥˙µƒæÞ÷¯£¨“ª¸c∂º≤ªø‰èà°£°±
ÒT∆‰”πþÄûÈ¥Àï¯åë¡À“ª∆™ï¯‘u£¨ï¯‘u÷–µƒ“ª ◊‘䣨å¶À˚ÇÉ∑ÚãDÇz‘⁄åW(xu®¶)–g(sh®¥)…œµƒ∆D–¡∞œ…ÊΩo”Ë∏þ∂»∏≈¿®£∫°∞É…√¸œý“¿èÕ(f®¥)œý¶£¨∆DÎyøý∂Ú≤°ûƒ(z®°i)”ý°£∫ÆüÙπ≤嶗–Ωõ(j®©ng)æÔL(f®•ng)—©…ÚÈTÕ–∏∂≥ı°£»f¿ÔÍP(gu®°n)∫”å§≈f€E£¨é◊Èg¬™ “åë–¬àD°£èƒΩÒ≤ªÿì(f®¥)ΩzæIᯣ¨’’“´ÂæÂ≠”–æÞﯰ£°±
£®±æŒƒ¸SƒÐ•’’∆¨”…π åm≤©ŒÔ‘∫—–æø^ÜT‘∑∫ÈÁ˜Ã·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