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巍,系2022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者、四川大學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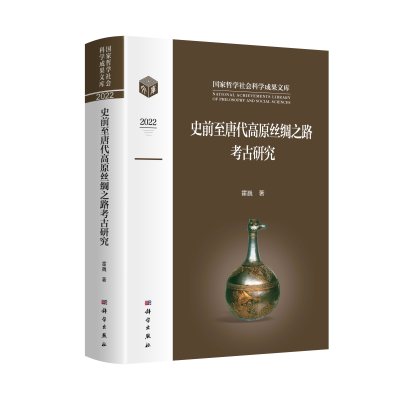
一提到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人們的腦海中往往會出現連綿不絕的雪嶺、荒原、沙漠這樣的自然景觀。難以想象的是,早在史前時代,人類不僅已經踏上了這片高原,而且開始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與交往,開拓出最早的高原通道。
如所周知,“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的本義是指代漢代中國通向西方的一條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后來,這個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發生變化:在時間維度上,人們意識到事實上早在漢代以前,已經有了以中國中原地區為出發點的東西方交流,因而從漢代一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時代,也向后延續到漢唐宋元以后,將不同時代的東西方交流路線都納入其中;在地理空間上,突破狹義的陸上絲綢之路(也稱之為“沙漠絲綢之路”)空間范圍,提出更為北方的“草原絲綢之路”和南方以海上交通為主的“海上絲綢之路”,以及區域間形成的“西南絲綢之路”等不同概念。
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外很少有人將中國西南地理空間上極為遼闊、地理位置上極其重要的青藏高原納入這個體系中來加以考慮。從青藏高原史前時代到大唐吐蕃時代,再到以后各個歷史時期,隨著西藏考古領域的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的不斷深入,有關青藏高原與外界交往、交流的物證也越來越多,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都與交通路線有關,甚至不少重要的考古發現都涉及唐代以來著名的國際線路的開鑿,中外高僧、使節、商人、軍隊各色人等在這些道路上往來等史實。
三十多年來,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支持下,我們深入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以堅忍不拔的工作意志和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這為本項目研究的開展提供了大量實物證據,奠定了堅實的研究基礎。
那么,應當如何評價和認識本成果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學術價值呢?其一,我們所要討論的“高原絲綢之路”的時代,并不僅僅局限在以絲綢貿易為主從而形成所謂“絲綢之路”的漢代,而是包括了從史前時代開始以來青藏高原地區與外部世界(包括外國與中國內地)交流往來的路線;其二,這些不同時代的交通路線既有主要干線,也包括若干重要支線,實際上已經形成一個交通網絡;其三,這些路線既有外向型的國際通道,可以直接通向今天的外域,又有內向型的通道,從而將這些通過青藏高原的國際通道和起點在中國內地、沿海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等連接在一起;其四,這些路線在歷史上所發揮的功能均不是單一性質的,它們與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傳播都有著密切關系,往往都具有復合性的功能。
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考古發掘工作不斷給研究者提供新鮮的實物史料,國內外學術界對于絲綢之路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狹義的絲綢之路概念,而是將其大大地加以拓展。這不僅是學術視野的擴展,也是理論、方法上的進步。而人類在青藏高原的拓殖和交往、交流與交融從而形成的交通路網,更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
雖然青藏高原考古工作起步較晚,但近年來西藏考古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從史前時代直到漢唐時代都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其中既有和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直接相關的大量漢晉、唐代的絲綢殘片;也有歐亞大陸和海上貿易中常見的寶石、珠玉等裝飾品的組件;出土金銀器中有不少系仿制中亞地區波斯薩珊王朝和粟特系統的金銀器;還有最能體現歐亞草原文化色彩的大量裝飾在金銀器上的有翼神獸、大角動物、馬與騎手等紋飾圖案。在一些文獻記載的重要交通要道上,還發現了和唐代中印交通直接相關的唐代使節王玄策出使印度時所鐫刻的《大唐天竺使之銘》摩崖銘刻,更是提供了印證、補充、完善文獻史料所載漢唐絲綢之路的重要考古實物。
絲綢之路在雪域高原的延伸,不僅是人類拓殖這片號稱“世界屋脊”的歷史見證,更是高原各族人民的偉大創造,使之形成交匯于“一帶一路”上的重要節點,也成為青藏高原聯系祖國內地和周邊地區的重要紐帶。高原兒女通過這些交通路網,如同石榴籽一般與祖國緊緊相擁,從不分離,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