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涌泉,系2022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者、浙江大學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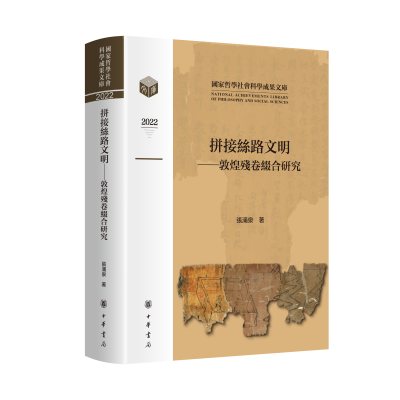
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古代寫本文獻的大發現,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震動了整個世界。它們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也是絲路文明最寶貴的實物遺存。然而,這些珍貴的絲路文明遺存,多是以身首分離的狀態呈現在世人面前,亟待修復和綴合。《拼接絲路文明——敦煌殘卷綴合研究》正是第一部敦煌殘卷綴合研究的著作。本成果的創新和突出的學術建樹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藏經洞文獻的性質提出了新的觀點。藏經洞文獻的性質及藏經洞封閉的原因,長期以來困擾著海內外學術界,堪稱世紀之謎。本成果指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經的場所有“經藏”與“故經處”之別,“經藏”就是三界寺的藏經處,而“故經處”則是用作修復材料的“古壞經文”的存放地,亦即后來的藏經洞。后唐長興五年(934年)左右,后來擔任敦煌都僧錄的三界寺僧人道真開始了大規模的佛經修復活動,很多敦煌寫卷中都留下了修復痕跡;藏經洞就是道真匯聚修復材料的“故經處”。那些經過修復配補成套的經本,“施入經藏供養”;剩余的復本及殘卷斷片,則留在“故經處”作為配補或修復材料備用,并最終成為我們見到的藏經洞文獻。藏經洞的封閉,則很可能與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復工作結束有關。我們通過對業已刊布的敦煌文獻的徹底全面調查,有力證明敦煌藏經洞文獻確實是來自“諸家函藏”的“古壞經文”,匯聚的目的是“修補頭尾”,即為拼接修復做準備。
第二,對敦煌殘卷綴合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闡述。根據對近百種共計32586號敦煌佛經寫本的統計,絕大多數佛經的可綴殘卷比例在25%以上,平均則達27.84%,數量巨大。這種“骨肉分離”的情況,不但不利于寫卷的整理與研究,也嚴重干擾了殘卷的正確定名和斷代。正因如此,敦煌殘卷的綴合成了敦煌文獻整理研究“成敗利鈍之所關”的基礎工作之一。本成果還從恢復寫本原貌、確定殘卷名稱、確定殘卷版本、推斷殘卷時代、明確殘卷攸關方、明確殘卷屬性、分辨殘卷字體、判定殘卷真偽、破解藏經洞文獻之謎等九個方面對敦煌殘卷綴合的意義作了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第三,提煉歸納了敦煌殘卷綴合的程序和方法。在前賢的綴合成果特別是本書作者綴合實踐基礎上,本成果提煉出了敦煌殘卷綴合的基本程序:首先在全面普查的基礎上,把內容相關的寫本匯聚在一起;其次把內容直接相連或相鄰的寫本匯聚在一起,因為內容相連或相鄰的殘卷為同一寫本割裂的可能性較大;最后再比較行款、書跡、紙張、正背面內容,以確定那些內容相連或相鄰的殘卷是否為同一寫本之割裂。接著,我們又從內容相鄰、碴口相合、字體相同、書風近似、抄手同一、持誦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類似、殘損相似、版本相同、裝幀相同十二個方面,對與殘卷綴合密切相關的關鍵要素舉例作了說明。
第四,發現了大批可綴合殘卷。我們在對世界范圍內業已刊布的敦煌文獻圖版全面調查搜集的基礎上,首先對其中近百部佛經作了窮盡性的定名、綴合、編目等工作,并在前賢綴合的基礎上,新發現可綴合殘卷達6499號,同時糾正了前人在定名、斷代及屬性、字體、真偽判定方面的大量疏失。如2019年7月14日,伍倫7號拍品《金剛經》殘卷以402.5萬元人民幣的高價成交,一時引起轟動。該卷為敦煌學家及文物鑒定專家周紹良舊藏,卷前有著名書畫家及文物鑒定家啟功題耑并鈐印。原卷卷軸裝,前缺尾全,存9紙181行,行間有非漢文夾注。敦煌學家方廣锠敘錄稱:“在3600多號敦煌遺書《金剛經》中,此種在漢文經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謂第一次漢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見證,彌足珍貴。”作為行間有非漢文夾注“唯此一件”的孤本,又有這么多重量級學者經眼鑒定,其珍稀和重要性毋庸置疑。后來我們在普查時,發現此號前可與北大敦20號綴合,從而使這一海內孤本得以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極大提升了它們的文獻和文物價值,而且也為絲路文明的交匯交融提供了鮮活的實物佐證。
第五,基本摸清了相關敦煌文獻的家底。在綴合工作正式展開之前,我們對所有已刊布敦煌文獻圖版作了窮盡性的調查和數字化,建立了數據庫,并給其中4000多號未定名殘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了敦煌文獻的家底。本成果每種文獻下一般包括引言、新綴、簡目三部分,其中的簡目就是為該文獻敦煌本的收藏及綴合情況所作的草目,這個草目是所收每種文獻目前為止最為全備的目錄,并且一般按存文內容先后及完整度排序,利用方便,對進一步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
自2007年第一篇敦煌殘卷綴合的論文發表以來,我們已經在這個領域耕耘了十五個年頭,很多年輕教師和博士、碩士研究生先后加入我們的隊伍。通過全面的普查和類聚,摸清了家底,明確了敦煌文獻的性質,并有計劃按步驟對敦煌殘卷進行了系統的綴合。當看到原本“骨肉分離”的敦煌碎片殘卷經過我們的拼接最終“團圓”的時候,一種巨大成就感和喜悅感充盈心間,讓人激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