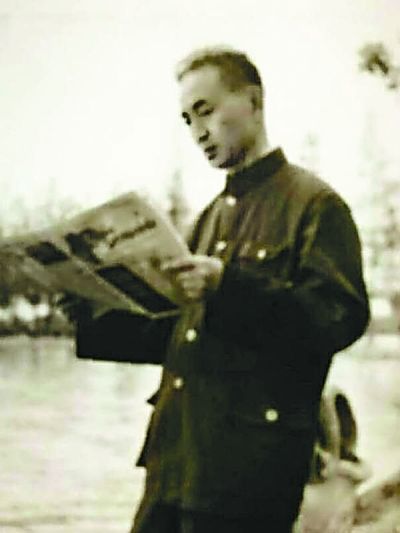
吳林伯先生在讀報 光明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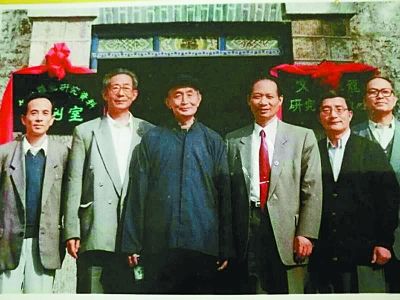
吳林伯先生參觀文心雕龍研究資料陳列館并與陪同人員合影 光明圖片

吳林伯先生與夫人 光明圖片
吳林伯先生一生追求,唯有學問二字。教導門人弟子說,“為山不虧一簣,窮理止諸自足”,宜“以高度韌性自勵”,“非議再多,堅定不移;處境再窘,堅定不移;工作再忙,堅定不移;困難再大,堅定不移;成績再好,堅定不移”。吳先生這樣教導我們眾弟子,而他更是身體力行。吳先生治學,精益求精,堅韌不拔。《文心雕龍義疏》是吳先生關于《文心雕龍》研究的代表著作,從撰寫到成書前后40余年,成書以后,又不斷更易。吳先生在《文心雕龍字義疏證·自序》中說:“余齒在志學,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習其儷辭而已。迨入本師馬一浮先生之門,朝夕親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為論文之作。于是請益問難,載歷寒暑。雖謏聞陋見,未能知類通達,而簡練揣摩,要亦粗識微言;重以古、今舊說,義多不愜,唯恐是非無正,使天下學者疑;故搦筆和墨,撰述《義疏》,歷四十二年而定。”又在《文心雕龍義疏·自序》中說:“余撰《義疏》,屢移寒暑,熔意練詞,不知所裁,常恐醬瓿之譏;然知難而進,舊典攸昭,妙識所難,其易將至,先難后獲,自然之數也。且不遠千里,擇師而事,終入馬先生之門,執贄請為弟子,親承音旨,不同研味遺言,探賾索隱,日不暇給、知至至之,欲與幾也。夫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玩懌方美,簡練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進而不知退,旁通發揮,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匪解,俾學有輯熙于光明。”《文心雕龍義疏》撰寫的甘苦,正是吳先生一向堅持的學術態度和學術良心。
吳先生恪守馬一浮先生治學的一貫,強調從經學入手,而守專門之學。吳先生在《論語發微·自序》中說:“昔仲尼通治六經,自以熟知其故,并應機授教,語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倫理、文學諸科,靡不畢具,包蘊可謂宏富矣。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因名之曰《論語》。學者當先求之,庶幾能明六經指歸。”吳先生自云二十余歲開始往來于川、湘、京、滬、齊、魯間,即首鉆《論語》,《論語發微》即為吳先生一生鉆研《論語》的總結,該書對《論語》中前人時賢所未發掘之義理訓詁給予訓釋,切實做到了不剿說、不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吳先生曾著文回憶馬一浮先生的教誨,提及馬一浮先生談論專門之學的重要,說:“學問之道,貴以專耳。惟專然后能集中精力,鉆研一點,深造自得;泛覽無歸,勞而少功。乃如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之徒,皆專攻辭賦;孔安國、服虔、包咸、鄭玄、馬融之屬,皆專攻經術。以其專心致志,切磋琢磨,眾隱盡變,故斐然成章,蜚聲翰林,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吳先生受馬一浮先生啟發,而選定《文心雕龍》為自己終身專攻,《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中又說:“西京經生,特重于專,其治《毛詩》,則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專之至也。陋儒記誦漫漶,博而不專,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所不能也。”自吳先生選定《文心雕龍》作為研究對象,從此,緊緊圍繞著《文心雕龍》這個題目,遍考先秦漢魏六朝載籍,無所不讀,并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龍》這部有關先秦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偉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績。
吳先生崇尚《漢書·儒林傳》所謂“樸學”傳統,而謂“樸學”,即“實事求是”之學。吳先生特別強調《漢書·景十三王傳》中河間獻王劉德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吳先生嘗撰有《簡論兩漢之學風》一文,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還未曾刊布,曾以書稿示我,命我誦習,我曾手抄一遍。吳先生以為,“‘樸’之言實,實則不浮,云胡為實?曰上山采銅,下井取礦,作文必讀文,著書必讀書,自感性到理性,由個體至總體,過此以往,語不虛設,春發其華,秋登其實,充盈而有光輝。且書不范圍于文字,自然、社會,亦皆書也。讀之未遍,妄下雌黃,紕繆差失,見笑大方之家”。吳先生又說,“不讀書而能研究著述者,蓋有之矣,余未之聞也”。《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回憶馬一浮先生教學生讀書法,“則開具群籍,兼經、史、子、集,并以六合之內,亦是一部大書,不可不讀。不獨破萬卷,下筆難以入神”。
吳先生信守《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進德修業。”馬一浮之《泰和宜山會語》有《君子小人之辨》,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人成為君子,而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區別,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類以言之,只是仁與不仁,公與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區別,未有如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記載,1957年春,馬一浮先生至曲阜闕里朝孔,吳先生與同門高贊非請見,馬一浮先生說:“讀書之道無他,求其反身修德,懲忿窒欲,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履而行之,荀卿所謂‘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讀書必改變氣質,非徒記其文句以為談資耳”。吳先生執君子之業,守君子之道,以人為善,不與人為惡。善修容儀,不內顧,不親指,不厲言厲色,泰然莊嚴。博覽古今,淡漠名利,不趨炎不附勢,不與世俗名利之徒往來。見諸弟子,莊嚴持重,偶有莞爾一笑。眾弟子稱呼吳先生必曰“先生”,不可稱“老師”。吳先生與弟子告別,弟子鞠躬,吳先生也必定以鞠躬還禮,俯仰優雅從容。
吳先生在生活上極其節儉,但是,對學問卻永遠不滿足。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成書后,除部分公開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為武漢大學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頗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1984年《光明日報》曾有專版介紹吳先生的研究成果。吳先生在《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中說他完成《文心雕龍義疏》以后,“為時流謬許,余以天道惡盈,不自滿假,盡力而為,功庸弗怠”,“昔仲尼俛焉孳孳,鍥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學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余師范賢圣,亦將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誤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為吳先生讀書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文心雕龍義疏·自序》說:“不懼我書與糞土同損,煙燼俱滅;亦不冀君山復出,以為絕倫必傳,好學修古,實事求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吳先生治學,強調學術創新的價值,并把創新和恪守師法結合起來。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歐陽竟無大師的師生之爭,熊十力先生是歐陽竟無大師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識論》,與老師的意見相左,但不影響熊十力先生對歐陽大師的尊師感情。類似的例子,先生還舉劉向、劉歆父子為例,劉向是今文學者,而劉歆則服膺古文學。吳先生認為,這種區別,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動學術進步。吳先生在《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中論述創新的重要時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應人,大亨以正,四時成而文明說,革之為義大矣哉。”
吳先生一生手不釋卷,每讀書,必于書中留白處留下批注,為了便于批注,先生所購書,多為線裝書,多次誦讀,每有新見,則加新批注,有修改,則換一種墨水。翻開吳先生的藏書,五顏六色的批注撲面而來,而宣紙的不滲透的優點就顯示出來了。到了晚年,吳先生才開始整理批注,謄抄在稿紙之上。20世紀中期以后,批判傳統的政治氣候和社會風氣,使吳先生的讀書習慣受到極大威脅。“文革”期間,據說有領導拿著吳先生的手稿譏笑,“文革”后,吳先生任教于武漢大學,因不喜與俗人周旋,被嘲笑為“冬烘先生”,也有人認為吳先生的學術方法過時了,但吳先生堅定不移,泰然如常。
吳先生對現實社會之權勢人情,異常隔膜,但時事改易,人心叵測,吳先生一生坎坷,卻仍始終不改志士氣質,高尚其志。吳先生生前家中廳堂之上,高懸馬一浮先生畫像,每至忌日,必作禮拜,數十年不輟,而對門人弟子,時時牽掛。吳先生一生的行止,以及對先生和弟子的情懷,秉持了中國傳統士人的氣概。吳先生去世之后,近些年,人們逐漸注意到了吳先生的治學方法的價值和學術成就的影響,吳先生在九泉之下,或許可以欣慰了。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孔子與儒家文化研究所、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