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子青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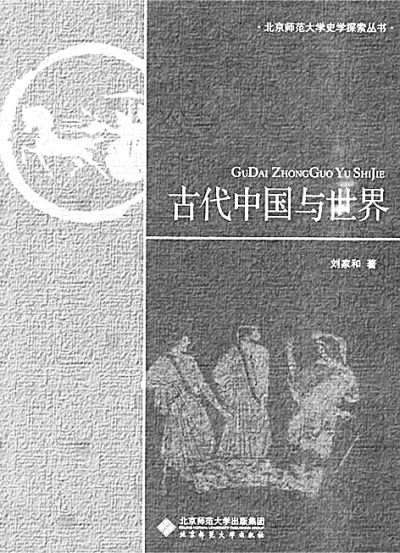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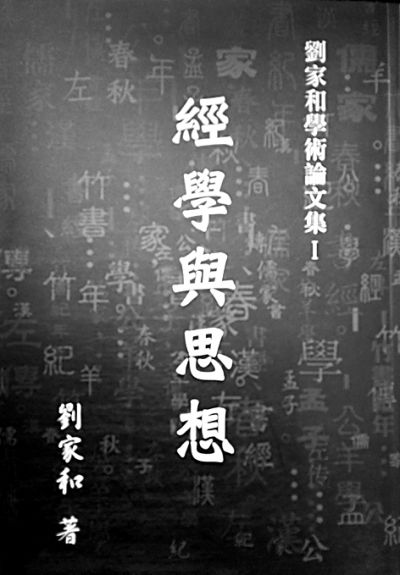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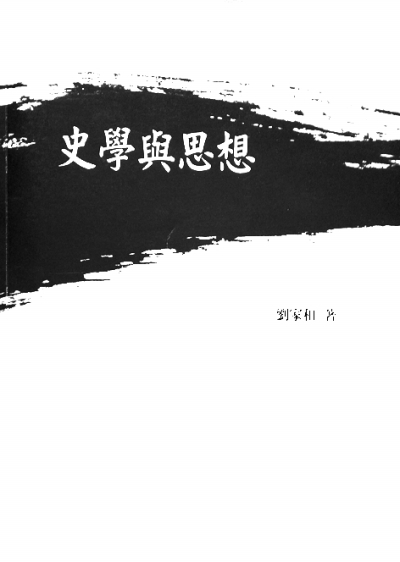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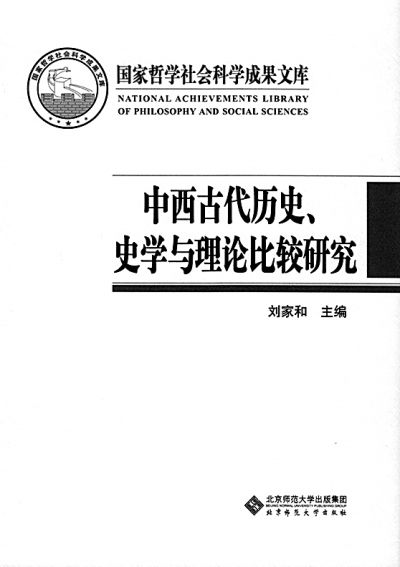
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一間2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里,有一位儒雅老者與我們如期相約。
白汗衫,灰馬甲,灰長褲,眼神謙遜,言語間透露出對其鐘愛一生的歷史學的敬意。他就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劉家和。
“你們覺得我氣色如何?”剛一見面,劉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問道,語氣中帶著幾分得意。事實上,幾天前他剛做完一個小手術,三天的流食讓劉家和稍顯疲倦。由于提前約好采訪時間,所以他堅持赴約,與大家共同分享他的學術人生。
顛沛之成長
“在國家危難之際,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熱愛更加真切。中國幾千年以來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斷斷不能舍棄!”
1928年,劉家和出生于江蘇省六合縣(今南京市六合區)。四歲多時,他被母親送進一家私塾讀書,接受《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的啟蒙。
1937年冬,南京淪陷,六合隨即也陷入日寇魔爪。小家和與母親被迫離開縣城,逃到集鎮的親戚家避難。當時,日軍飛機不時在南京附近的縣城或集鎮上空盤旋,老百姓終日提心吊膽。
有一天,劉家和與鄰居小伙伴一同前往私塾,不幸碰到日軍空襲。飛機一邊往集鎮扔炸彈,一邊用機關槍掃射。子彈從他身旁嗖嗖飛過,他幸運地未被擊中,但有的小伙伴卻不幸中彈身亡。“我是真的經歷了槍林彈雨!”憶及此,劉老的情緒略顯激動,眼眶有些濕潤。
集鎮也遭轟炸,只好再逃到農村。可是,在農村就既沒有家又無處讀書,堅信只有讀書才能使孩子自立成人的母親,還是決定回到縣城,并將小家和送到一所教會學校。
在教會學校里,劉家和第一次接觸到英語。課堂上,老師將鉛筆、書本、盒子放在孩子面前,以實物教會他們“pencil、book、box”。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教會學校解散,劉家和只能去補習學校,跟著老先生讀古書,《四書》《幼學瓊林》《唐詩三百首》的反復誦讀,為其后來的古文學習和研究打下基礎。
“在國家危難之際,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熱愛更加真切。中國幾千年以來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斷斷不能舍棄!”這是一個十四歲少年的自勉。
“那時候,我們讀書的心情就是都德《最后一課》中呈現出來的情愫。我們始終堅信中國不會滅亡,一定會取得最終的勝利!”劉家和的語氣鏗鏘有力。
劉家和在教會學校學英文用的是直接法,不學語法。補習學校里的英文教學除課文外,還專門有文法課。對于每個復合復雜句,都必須作圖解分析。就這樣,他從中國老師那里學到了一種嚴格的外文文法分析的訓練,由此也引發了劉家和對外文文法的終身興趣。
除了語法外,數學也帶給劉家和極大的觸動。“我見到數字常有一點發懵,可是一學代數,腦袋就開始活了,一學到幾何,就來勁了。”幾何學里的點、線、面、體,定義、公理、定理等等,一系列嚴密的推導系統,使他深切地體驗到邏輯論證的威力。
劉家和開始意識到,西方學術有一套不同于中國學術的思維方法,近百年來中國之所以落后挨打,與這種思維方法的缺乏有一定關系。
“中國人如果能學會用西方的思維方法反省自己的傳統文化,對本國文化會有新的認知,也會有助于文化的振興。”因為少時的學習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下展開,這也為劉家和后來從事中西比較研究埋下了種子。
到了中學,由于戰爭,學習斷斷續續,但劉家和從未中斷讀古書、學數學和英文。抗戰勝利后,他在南京作為插班生讀了三個學期。
劉家和想進一步上大學深造。可是,他對于物理、化學、生物等諸多學科,都不曾真正學過,考理科根本不具條件,所以只有選擇文科。
考取哪所大學呢?一位學長知道劉家和對古文的熱愛,鼓勵其考取自己所在的無錫國專,并帶領家和拜謁了幾位國學老前輩。此時,劉家和的內心深處又起了波瀾:愛中國固然要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但是,愛中國難道就不需要認識世界嗎?
就在劉家和猶豫之時,國專的另一位學長給他帶來一則消息:榮家在無錫興辦江南大學,將聘請錢穆等著名學者前來任教。
劉家和的心中有了答案。
恩師之教誨
“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在求知欲極為旺盛的階段遇到這些老師。就像一株剛要從泥土里向外冒出頭來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們所施與的智慧的陽光雨露。”
1947年秋,劉家和順利進入江南大學,并選擇了歷史專業。在史地系學習的這幾年,他選取了中外通史、商周史、秦漢史、哲學概論、邏輯學(當時稱理則學)、中國文學史、經濟學、微積分、倫理學、古文字學等課程,盡情吸收著知識的養分。
“錢穆當時開設中國通史和秦漢史,在他的課上,我時常會有醍醐灌頂的感覺。他善于從復雜紛繁的歷史事實中給學生說明一條清晰的要領,也同樣善于提出關鍵問題并加以點睛。”劉家和回憶說,“一次,我向先生請教老莊的問題。先生反問我:‘老子、莊子,孰先孰后?’我答:‘老先莊后。’‘有何根據?’答:‘莊書里有老聃,而老子里無莊周。’錢先生看我浮躁好辯,便囑咐我認真閱讀他寫的《先秦諸子系年》。讀了這部書,我才知自己在學問道路上還很膚淺,從此沉下心來。”
除了《先秦諸子系年》,錢穆還要求學生閱讀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梁啟超的同名著作。從這些著作中,劉家和明白了治史必重考證,治先秦史必須知曉清儒研究成果,而這一點也成為他治中國古史時一直信奉的原則。
“要學哲學,不能用常識來思考,要用邏輯來思考。”這是唐君毅的告誡。當時,唐君毅講授《哲學概論》和《倫理學》,為劉家和的學術思維開辟了一片新天地。他所講的黑格爾辯證法,更讓劉家和領略到西方哲學先驅的光芒,從此開始與黑格爾哲學逾一甲子的碰撞。
牟宗三講的是邏輯學,尤其是西方古典邏輯,偶爾講一些因明學和墨家邏輯。這門課與劉家和青睞的幾何學都是一種西方人所習用而中國人不常用的思考方法。
馮振講授文字學,讓自幼喜愛文字訓詁的劉家和更是興奮不已。跟著馮振學《說文解字》,逐字精讀,也讓他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訓詁研究上的成果。
1949年,江南大學史地系停辦,劉家和又重新報考了南京大學歷史系并被錄取。在這里,史家云集,韓儒林的《中俄關系史》、賀昌群的《魏晉南北朝史》、蔣孟引的《英國史》、劉毓璜的《社會發展史》等課程讓劉家和受益匪淺。可惜,由于身體狀況欠佳,在南大上了不到一年的學,他便被迫休學。
身體稍有好轉,1950年9月,劉家和就考取了陳垣主持的輔仁大學。在輔仁,柴德庚、金毓黻、漆俠、劉啟戈、陸和九的課,也使劉家和的史學知識儲備愈加豐富。
雖然受教時間不長,但是這些史學前輩的教誨令劉家和終生難忘。“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在求知欲極為旺盛的階段遇到這些老師。”劉家和形象地比喻道,“就像一株剛要從泥土里向外冒出頭來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們所施與的智慧的陽光雨露。”
研究之相通
“我沒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轉進’。對我來說,中國史和世界史并不是兩張皮,互相扯著,而是相通的。希臘史、印度史都是我的研究興趣,不過我想將其都融入到中外古史比較研究體系中。”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輔仁大學并入北京師范大學,劉家和也留在師大歷史系任教。不過,教的并不是中國古代史,而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世界史師資極度匱乏,系里領導看到劉家和的英文不錯,便安排其從事世界史的教研。
“從內心來講,您同意這樣的安排嗎?”
“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應該是中國古代史,但也是將中國放在世界的視角下進行研究。無論是中國史,還是世界史,我都不想放棄。”
既然決定了研究世界史,就得從外語上下功夫。英語和俄語是當時要求必須掌握的外語,如何能提高英文并學會俄文呢?劉家和的方法是對照學習。
先讀英文譯本的《共產黨宣言》,逐句作文法分析,到讀俄文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時,采用同樣的文法分析方法,然后再逐字逐句地對照英譯本讀,尋思其中的異同。經過幾個月的堅持,劉家和的英文與俄文水平都有所長進。之后,他又用同樣的方法閱讀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除了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助教任務外,劉家和還參加了世界古代史講義的初稿編寫以及外系世界通史(前半段)的教學工作。恰巧,當時北師大一附中一位教世界近代史課的老先生因病不能上課,劉家和又奉派到附中講課。
這對于剛留校的劉家和來說,壓力可謂不輕。他說,自己雖然挺住了,可是心里總想,這樣下去,哪里還有時間和精力專心作研究?
當時,劉家和的住處與歷史學家白壽彝的家離得很近,二人在上下班的時候經常會搭乘同一輛公交車。有一次在車上,白先生詢問他近來工作和學習情況,劉家和把自己的擔憂說了出來。白先生笑著說:“這不是壞事,是好機會!”
原來,抗戰時期,白先生攜家帶口,只在一處教書,薪水不夠養家,所以就在多校兼課。“這是增長知識和開闊視野的大好機會,博學慎思,力求一貫。再忙也不能不思考問題,教書就是發現和積累問題的機會。”聽了這些話,劉家和頓覺豁然開朗。從此,系里有各種工作找到劉家和,只要力所能及,他一定努力去完成。
在教學工作中發現并積累要研究的問題,這一點特別重要。劉家和在講授世界古代史時,對西方文明的源頭希臘充滿興趣,還主動承擔了講義中古希臘史部分的編寫工作。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史學界,古史分期問題討論正酣,一些學者為了做比較,將研究觸角拓展到古希臘斯巴達的“黑勞士”問題,這恰好為劉家和指明了研究希臘史的方向。
1955年秋,蘇聯專家格拉德舍夫斯基應邀到東北師大講學,并開設了世界古代史教師進修班,面向全國招收中青年教師。經過考試,劉家和進入這個班學習,為期兩年。當時,在東北師大任教的林志純名義上是以中國專家的身份配合蘇聯專家工作,實際上承擔了大量的論文指導工作。
根據當時規定,學員必須完成一篇畢業論文,答辯通過后方能頒發畢業證書。林志純提醒各位學員,論文題目越早定出越好,因為可以贏得相對較長的時間來準備、寫作和修改。早有準備的劉家和以《論黑勞士制度》為題,在查閱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認真寫作、反復修改、精心打磨,最終完成一篇近八萬字的論文,并由翻譯組老師全篇譯為俄文請蘇聯專家審閱。
這篇論文在答辯會上得到蘇聯專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和林志純等中國專家的一致好評。
此刻,初嘗“比較”滋味的劉家和卻涌入另外一個念頭——將比較視野擴展至另一文明古國印度。為此,他從漢譯佛經目錄入手,以小乘經律為基礎,大量閱讀,同時閱讀英譯(少量俄譯)印度古典文獻,以資比對,察其異同。
正是用這種系統而扎實的學術方法,1962年,劉家和寫作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種姓制度觀》一文,被白壽彝發現后,舉薦發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次年又有《古代印度的土地關系》也發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
白壽彝曾想推薦劉家和,跟著季羨林學梵文。可是,隨之而來的一場場政治風暴,白、季二位先生都成為“反動權威”,梵文學習不了了之。
“文革”結束后,季老鼓勵劉家和繼續進行古印度史研究。可此時,劉家和已經進入白壽彝主持的史學研究所,一方面致力于白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這一浩大的史學工程,另一方面開始從事古史比較研究,專門研究古印度史已無可能。
任繼愈當時正準備整理出版《中華大藏經》,希望劉家和可以參與其中。劉家和征求白壽彝的意見后,覺得歷史學畢竟是自己的主要精力所寄,婉言謝絕了。
曾有師長跟劉家和開玩笑:“你又從世界史逃到中國史去了。”
“我沒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轉進’。對我來說,中國史和世界史并不是兩張皮,互相扯著,而是相通的。希臘史、印度史都是我的研究興趣,不過我想將其都融入到中外古史比較研究體系中。”劉家和如是解釋。
史家之擔當
“中國人是在運動中把握真理,西方人是在永恒中把握真理。人類不能沒有在永恒中把握真理這條路,也不能沒有在運動中把握真理的能力。從柏拉圖起,西方人就有一個不信在變化運動之物中能把握真知的習慣。我就寫文章說明這個問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劉家和便正式與中外古史比較研究“牽手”。
在劉家和看來,從事比較研究,必須具備兩大條件。第一,對于所要比較的對象有總體的了解;第二,從原始資料入手,研究至少某一文明的歷史,并取得一些成績。
參照這兩項條件,劉家和剖析自己。對于世界古代文明史,他已經有了大體的了解和把握,對古希臘和古印度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中國古文明是我們自己的文明,是我的精神自幼即寑饋于其間的文明,自覺理解較深,也具備從原始文獻入手做研究的能力,最需要的是在中國古史方面做出一些切實的研究成果,積累起一定的研究經驗。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具體的研究取向,就是把中國古史的研究同經學文獻研究結合起來,這是為了從源頭上探尋中國古史的精神來龍。”劉家和在自傳文章中回憶了這段心路歷程,順著這樣的研究路數,他在史學界自成一家。
2014年8月,一篇題為《試說〈老子〉之‘道’及其中含蘊的歷史觀》的文章在《南京大學學報》第4期刊出。殊不知,這是一位自少年時就開始讀《老子》的學者發表的第一篇關于《老子》的文章。他說,自己十幾歲就讀《老子》,讀了不知道多少遍,卻一直沒有發表相關文章。
文章中,劉家和解讀了“老子的道的內在矛盾性”,認為老子的“道”并非黑格爾所言的“絕對的空虛”,而是從普遍到具體的發展過程,從而對黑格爾的挑戰做出了有理有據的回應。
“我學了一輩子黑格爾,受益于他,現在要挑戰他。”嗓音略微激動,一語一停,劉家和的眼神中,透露出堅毅、執著與自信。面對黑格爾對中國文明的挑戰,這位有些倔強的老人通過文章對黑格爾的論斷予以反駁。但反駁與挑戰并非最終目的,他希望借此了解更有意義的東西。
“中國與西方學術最根本的區別,不在于哪一方有無理性的問題,而在于各自理性的結構的差異,中國是歷史理性占主導地位,西方是邏輯理性占主導地位。”劉家和認為,比較研究中,最深度的比較就在于此。
“中國人是在運動中把握真理,西方人是在永恒中把握真理。人類不能沒有在永恒中把握真理這條路,也不能沒有在運動中把握真理的能力。從柏拉圖起,西方人就有一個不信在變化運動之物中能把握真知的習慣。我就寫文章說明這個問題。”
2013年,劉家和主持編寫的《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的比較研究》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這是目前國家層面表彰社科研究成果的唯一榮譽。
“史學研究不能回避重大問題的挑戰,創新正是在成功回應挑戰中實現的。”在出席該項目基金評審工作會議時,劉家和說,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一種“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勁頭。其中,“上窮碧落”是指在理論方面要站得高,“下黃泉”是指在文獻方面要鉆得深。
對于自己的學術研究,劉家和總結為三大張力。橫向層面上中西方比較研究的張力;縱向層面上的“二非羅”張力即哲學(Philosophy)和語言學(Philology)的運用相得益彰,同時也是學問深度與廣度的張力;再就是有用之用與無用之用的張力。
有人問劉家和,為什么年紀這么大了,還筆耕不輟,一直在發表文章?究其原因,在于他“心里有事,睡不著”。
老者的“心事”,來自從業歷史研究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的使命感——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找到二者差異的源頭,為中華文明存在的意義和應有的地位正名,也為更好地理解中華文明的優勢與缺陷,更要通過比較來思考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這項工作絕不是我能做得完的,一輩子都做不完,我怎么能休息呢?”
使命感使劉家和多思而嚴謹。他說自己作品很少,談不上著作等身,“別人寫10篇,我只寫1篇”,因為他“只想把問題搞清楚”。
2014年,劉家和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三篇文章,其中《傳承和創新與歷史和史學》一文在1998年便完成了草稿,直到2013年11月才最終修改定稿交給編輯部。
劉家和把自己的目標定得很高,坦言自己活得很累。他說自己是“活該”,是“不可救藥的”,卻義無反顧地走在比較研究的道路上。“別看我現在86歲了,就是再活80年,我都達不到自己的目標,我是一個達不到目標和理想的人,我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了!但不管多么困難,我都要學。”
現在,劉家和依然像上大學時那樣,對知識如饑似渴。盡管對中西古史比較做出了不凡的貢獻,他卻覺得自己的真正價值在于精神層面:他的追求、使命感。
陸游有詩云,“放翁百念俱已矣,獨有好奇心未死”,這是劉家和的座右銘,也是他學術心態的真實寫照。
謙遜之風骨
“我就像這臺又老又舊的手機,雖然現在還沒關機,但是時間已經不多。不過,看到了你們年輕人,我便看到了希望。”
劉家和這一代學者,成就耀眼,而這種“耀眼”的背后,卻是他們衣食住行的樸素。
“一棟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四層單元小樓,劉家和與老伴家住二樓。走進客廳,一張沙發、一張寫字臺、一張茶幾,此外近一半的空間,是書柜;而沙發、寫字臺上都堆放著摞成小山的書籍與學生論文。
劉家和輕易不讓他人去家中拜訪,因為“家中已‘無地自容’”。
尊重學生,因材施教,是劉家和為師的標簽。
曾師從劉家和攻讀博士學位的蔣重躍,如今已是先秦思想史領域的著名學者。他回憶道:“劉先生善于發現學生的優點,為學生著想,幫助學生建立信心,讓學生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
定期與學生談話、交流,了解學生的想法,是劉家和帶學生一貫堅持的原則。“我希望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知識背景和個人興趣確定選題,重在啟發他們的靈感。”
這么多年來學生送來請教、審閱的論文,劉家和都一直保留著,因為“學生的論文都是他們的心血,可不能扔啊。”
“劉先生的課,從根底入手,以理論升華,傳學術研究之道,開原創思維之路,給人極其深刻的印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楊共樂教授如此評價劉家和的教學和研究。
知識淵博,是學者對劉家和的一致評價。
蔣重躍直言,劉先生興趣廣泛、善于思考,除了史學,對其他領域的知識也有鉆研。他曾下大功夫研讀《資本論》,深入思考許多數學問題和經濟學問題。
與劉家和經常交流學術問題的人,都清楚他“由小學入經學,再由經學入史學”的學術路數。
“對于中國的經學、小學、史學等,劉家和都可以在高層次上與專業領域的學術大家交流。這是現在很多學者所不及的。”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瞿林東向記者說。
劉家和喜好《說文解字》,他在家備有不同版本的《說文解字》,其中中華書局印制發行的簡本有兩本。
歐陽修說其平生所做文章,乃“馬上、枕上、廁上”,劉家和“深諳此道”。一本《說文解字》與中英文字典一起放在床頭,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翻一翻,認識幾個不熟悉的字詞。另一本則放在衛生間水箱上,內置書簽,每次看兩頁。老伴開玩笑說:“家和,你認得幾個臭字。”
為人謙遜,是劉家和給周圍人的印象。
瞿林東在學生時代曾經聽過劉家和開設的課程,所以尊稱劉為老師。但劉家和不以為然,認為那是過去的事,現在大家都是同事和朋友,直接稱自己姓名便好。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時,不管與會人多大年紀,劉家和都會以禮相待。
“儒雅之風,謙和之舉,可見一斑。”瞿林東如是評價。
業余時間,劉家和不看戲,不看電影,甚至不讀長篇小說。他的休閑方式同樣“中西合璧”——最愛玩味傳統詩詞,欣賞西方古典音樂。
疲憊的夜晚,老人會把燈調暗,躺坐在沙發上,雙眼微閉。一段旋律飄然入耳。音樂循環播放,幾十次地反復聽,讓自己融入其中,仿佛整個人已伴隨著音樂遨游古今中西。
曾上過教會學校的劉家和喜歡哼唱圣誕歌曲Silent Night:“Silent night,holy night……”閉目傾聽,精準的音高,平穩的嗓音,讓人不覺這是一位耄耋老人。
采訪收尾,劉家和拿出一款破舊老人手機自比:“我這臺手機還沒關機,但是時間已經不多。不過,看到了你們年輕人,我便看到了希望。”(本報記者 周曉菲 徐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