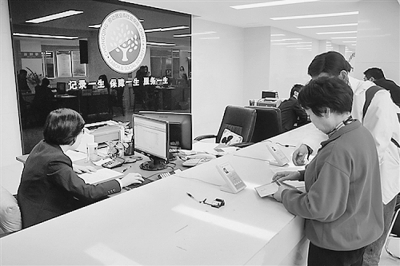
強調社區的自我管理、推動實質性社區的發展,是新一輪的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圖為重慶市南岸區南坪街道“社區公共事務中心”的工作人員正在為社區居民服務,該中心將社區的大部分行政職能加以集納、整合,以求歸還社區的自治功能。 圖片來源:重慶日報
“改革”與“市場”,無疑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關鍵字眼,而“治理”的出現,則成為整個報告的亮點之一。這幾個詞涉及到當下中國一個非常緊迫的命題:在實現市場資源配置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的轉變過程中,如何通過社會治理體制等各項具體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建設?
作為優化資源配置的一種手段,優勝劣汰是市場的本能。如果說市場會帶來這樣或者那樣的風險,原因并非市場有錯,而在于我們并沒有建立與市場相匹配的國家治理體系。在未來更加深化的市場改革中,建立與市場相匹配的國家治理體系變得非常重要。這一建設指向三個基本任務:一是在政治層面,完善政治協商機制,通過程序來強化公共權力責任,以應對社會壓力;二是在行政層面,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直接回應社會需求,消弭市場競爭所帶來的過度懸殊的利益分化;三是在國家與社會交界處,為社會組織發展提供制度便利,增強社會的自組織能力。
和社會管理體制不同,社會治理體制的提法強調的是多元化手段的使用,強調的是雙向對等溝通。在一個完善的社會治理體制中,政府、市場、社會將構成良性合作關系。因此,與帶有一定管控意味的社會管理體制比較,社會治理體制更關乎“社會”。在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和全新的社會治理概念背景下,新一輪的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有幾項重點工作需要特別指出:
重點一:啟動社會政策改革議程。在以往的改革中,我們經常說經濟政策,很少說社會政策,原因在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做大蛋糕”,但今天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則是“分好蛋糕”。事實上,隨著市場化的推進,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社會政策領域的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尚未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如此,一些地區間的公共服務差異還有所加大。為此,我們必須導入“社會政策”視角,重啟社會政策改革議程,并進行專業化的、精細的社會政策設計。顯然,新的社會政策領域的改革,是三中全會報告所折射的理念。
重點二:推動實質性社區發展。社區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元和重要場域,但在我國改革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社區并不是扮演社會生活共同體的角色,而是主要發揮著國家管理單元的功能。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社區的功能。這其中,要強調社區的自我管理。當然,社區自我管理并不意味著社區不屬于公共管理的范圍,比如商品房小區的公共安全也屬于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產品,而重要的是,在政府供給的同時,社區也可以通過自組織的形式補充供給。如何發揮社區的這種自我管理功能,需要社區居民具有充分的社區精神和志愿精神。
重點三:關注業主議題及其相關的社會沖突。在中國住房改革之后,國家不再直接參與房地產領域的分配活動,城市居民得以根據自身經濟實力和住房需求選擇住房,“業主”一詞漸入人們視野。從制度層面來看,業主議題不能再混同于一般的公民個體,而應該成為單獨議題,并以此為基礎理順我們現有的各種相關法律體系。必須在物權法的精神下,梳理現有各種地方物業管理法規,完善對業主物權的保障體系,在制度層面上疏導可能發生的各種業主物業沖突。在鄰避沖突解決過程中,要特別關注的是,必須在法律和制度上將各種具有鄰避效應的公共設施列入決策過程中,不能再以模糊的“尊重多數人利益”而犧牲鄰避設施所涉及的少數人利益。
重點四:大力發展基于家庭服務的社會組織。家庭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社會關系紐帶,也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感情紐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將產生很多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政府往往會由于公共服務能力的有限而無法回應,由社會組織來承擔則是最好的選擇。對我國而言,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這么多年,傳統家庭互助體系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并潛存著巨大的社會隱患。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注家庭在社會轉型中的需求,并對這類的社會組織進行培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重點五:推動有意義的公眾參與。“有意義的公眾參與”有三個特質:其一,公眾參與是否有明確的公共問題指向;其二,政府是否有可能針對不同群體設計不同參與方式并以此減少社會排斥;其三,這些參與能否形成某種實質性的結果。“有意義的公眾參與”其實反映的是政府與公眾打交道的誠意與技巧。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歐洲國家流行的卓有成效的公眾協商方法包括:居民顧問團、焦點團體、居民意見調查小組等等,并以此促成了良好的政—民互動效果。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雖然公眾參與無論在正式文件還是街談巷議中都是常被提及的術語,但對大多數居民而言,我們對除了投票、聽證會以外的其他參與技術依然非常陌生。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成熟做法。
重點六:用社會邏輯來解決社會問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社會領域的問題時經常重“堵”不重“疏”,重“處置”而不重“防范”,政治邏輯被直接應用于解決社會問題,導致原本可控的問題往往以高昂的代價解決。當前我們要樹立這樣的觀念:和諧社會也是存在沖突和分歧的,這些沖突和分歧可以通過制度化渠道紓解并被社會所容忍。我們要有勇氣并且學會用社會邏輯來解決社會問題。而在這方面,基層黨組織建設大有作為。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社會穩定體系建設研究”首席專家、中山大學教授)